疫情之下,数字技术加速社会重构
添加时间:2020-03-11 点击次数:873
疫情是对数字生存的一次极端压力测试,它将改变很多东西,特别是技术与人类的关系正在发生巨变,体现在对商业的改变,对信息的改变以及人与技术之间情感联系的改变。
在谈技术对社会的重构之前,我想先谈一下数字革命与前几次技术革命的不同之处。数字技术引发变革最根本的原因是信息成本的大幅降低。按照摩尔定律,每隔一年半到两年,信息处理效率翻一倍同时成本减半。半个世纪过去,在摩尔定律的预言下,各行各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的非排他性——信息可以被无数人分享,它不像冰激凌,我吃了,你就不能吃了;石油我烧了,你就不能烧了。信息可以被所有的人分享和使用。信息成本指数级降低与非排他性叠加,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参与度。每个人都成为信息的贡献者、分享者、受益者、被影响者和影响者。我认为这是数字革命最根本的原因。
纵观人类历史,前几次技术革命都是自上而下的,是从最富有、最具权势的群体慢慢向其他阶层扩散,但数字革命不同。我们看到,普通甚至中下等收入的人正在成为数字技术最积极的使用者之一,这与传统的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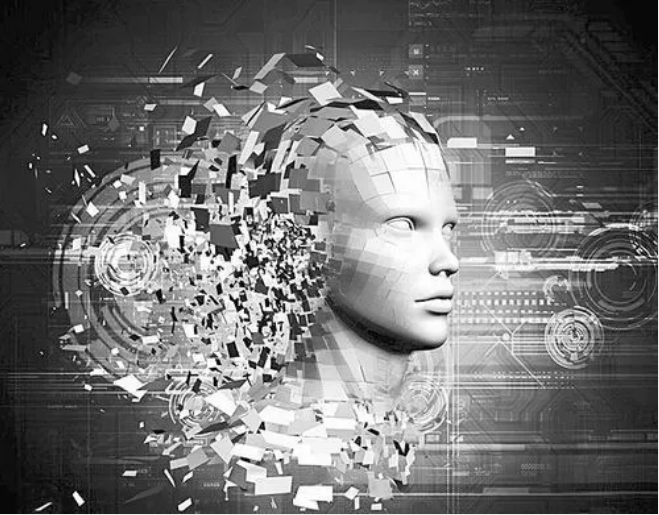 以电子商务为例,阿里淘宝村能够让很多居住在农村地区的普通人通过互联网参与到产品销售和购买。我们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只有小学以上的文化,一旦他参与到了电商,他的平均收入与同一村子里大学或者大专学历但是不介入电商的人群相比毫不逊色。也就是说,数字技术弥合了教育带来的机遇鸿沟,带来了很多可能性。这也是社会底层的、不富有人群,从农民工到老年人,都会拥抱互联网的原因。所以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或者说“互联网+”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普惠。
以电子商务为例,阿里淘宝村能够让很多居住在农村地区的普通人通过互联网参与到产品销售和购买。我们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只有小学以上的文化,一旦他参与到了电商,他的平均收入与同一村子里大学或者大专学历但是不介入电商的人群相比毫不逊色。也就是说,数字技术弥合了教育带来的机遇鸿沟,带来了很多可能性。这也是社会底层的、不富有人群,从农民工到老年人,都会拥抱互联网的原因。所以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或者说“互联网+”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普惠。
然而任何时候,新技术,特别是革命性技术诞生之初,人们都会有天然的抵御心理。一百多年前,中国在进行洋务运动、日本在明治维新。然而两个国家对技术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后来也因此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中国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思是技术只是一种工具。而日本是“全面西化”,甚至要“脱亚入欧”。历史证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不会因为接受技术就丢掉了民族性,反而闭关锁国,排斥新技术会带来更大的伤害。
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不仅仅停留在技术和商业上,我经常在思考:技术会在多大程度上重构我们的社会?
 我想谈几个方面,首先是企业组织的变革。本次疫情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压力测试,让原来很多线下可以做的事情不能做了。消费者不能出去线下消费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突然之间休克了。这时O2O服务、远程教育、远程办公开始爆炸性发展。这个习惯的改变,一直在缓慢发生,又被突然发生的系统性冲击大大提速,并且很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
我想谈几个方面,首先是企业组织的变革。本次疫情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压力测试,让原来很多线下可以做的事情不能做了。消费者不能出去线下消费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突然之间休克了。这时O2O服务、远程教育、远程办公开始爆炸性发展。这个习惯的改变,一直在缓慢发生,又被突然发生的系统性冲击大大提速,并且很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
企业和组织要进行巨大的变革来适应。有的企业会发现远程办公效率更高,这种企业往往是目标导向,给员工更多的灵活性,同时也做了更多早期的转型准备。有的企业发现效率更低了,这跟组织自身的特点有关,也和其和数字技术的结合程度有关。
不但企业内部,企业和用户之间的关系也有巨大改变。在这段时间我看到很多企业的商业模式在发生改变,都在向网上迁徙,而且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以后完全线下的业务越来越少。有一位做零售的企业家告诉我,零售如果绝大部分业务在线下,即便现在仍然不错,也不代表未来的方向,不会投资了。
 第二个是信息传播的改变。这次疫情的信息传播与公众应对是一次根本性变革,17年前SARS时没有做到,当时没有移动互联网,更不存在4G、5G。通过社交网络,我们飞快地获得关于传染病的相关知识。我们分享自己的情感,同时也分享谣言,之后再慢慢过滤。恐慌很多时候是源于未知,就像中世纪鼠疫引发黑死病,它导致欧洲数千万人死亡。当时信息完全缺失,普通民众完全不知如何预防和应对鼠疫,每天生活在巨大恐慌之下。
第二个是信息传播的改变。这次疫情的信息传播与公众应对是一次根本性变革,17年前SARS时没有做到,当时没有移动互联网,更不存在4G、5G。通过社交网络,我们飞快地获得关于传染病的相关知识。我们分享自己的情感,同时也分享谣言,之后再慢慢过滤。恐慌很多时候是源于未知,就像中世纪鼠疫引发黑死病,它导致欧洲数千万人死亡。当时信息完全缺失,普通民众完全不知如何预防和应对鼠疫,每天生活在巨大恐慌之下。
大半个世纪以前,经济学界有一场著名的辩论,是中心化的治理方式好?还是去中心化的治理方式更优。哈耶克的核心观点是,市场最核心的作用是把各种分散的信息能够整合在一起,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这个智慧的过程是中心化的治理方式无法替代的。
在观察疫情发展过程时,我经常想到哈耶克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在疫情中网络上有各种信息,有专家的,有政府的,有企业的,有民众的,就像一个市场一样,它把非常分散的信息聚合在一起。各方对这些信息不断吸收检索,直到找到认为合适的证据为止,这个过程就像信息的交易。但这个交易是有成本的,因为有些虚假信息需要过滤。这个时代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十几亿人投入参与的交流信息的场所。正面的地方是它会带来巨大的信息整合的价值,甚至在信息市场之上会产生一个思想市场。但它也会带来负面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降低虚假信息的外部性,要建立一个分辨和抵御假新闻的信息治理机制,帮我们更好的把信息分层。
第三个是重新定义人与技术的情感联系。有个寓言叫庄周梦蝶——我到底是在现实世界中还是虚拟世界中?这次事件给了我们一个比较极端的机会,技术一下子逼迫我们跟它们发生了更多联系,这会重新定义我们是虚拟的人还是一个现实中的人,以及我们对技术的情感联系。我曾经听到一个故事,因为疫情在家隔离,有人就会和自己的天猫精灵聊天,不是命令它去做什么,就是单纯的聊天。前一段时间,达摩院受一位失独母亲的邀请,用AI技术复原了故去女儿的声音来陪伴安慰这位母亲。罗汉堂还从心理学的角度评估了可行性。
如果没有数字技术,隔离中我们可能就买不到蔬菜水果,吃不到外卖,也看不到免费的《囧妈》。总而言之,疫情让很多人改变了对技术的态度和看法,从以前的不在乎甚至抵触,变成了接受甚至依赖。
当然也有不变的东西,我认为不变的是技术会继续解放人性。在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里面,技术与人结合的结果是人也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人必须像一个机器一样去跟机器配合,变成一个螺丝钉一样的东西,这是摩登时代里人的悲剧。后来出现的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也是把人当成工具,最大程度地压榨员工。梅奥的霍桑实验标志着人本主义崛起,此后企业家越来越意识到员工也是一种资本,一个企业的活力在于员工的创造力、一个企业的效率等同于员工协同的效率。另一方面,消费者越来越重要,生产是以消费者为核心来运作的。我们发现技术越进步,人类越解放。
 历史告诉我们,技术从来不会改变主体的本质,不会改变情感的本质,不会改变商业的本质,不会改变信息的本质,但是技术会改变产生方式,从形式到效率,都会改变。这是过去两百年来的趋势,我相信以后还会持续,技术会带来越来越多对人的解放,包括对人性的尊重,因为人变成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一个竞争力;但是技术也会带来新的挑战和不定性。这个事情一直在发生,我们能选择的,是学习更好地让技术造福人类。
历史告诉我们,技术从来不会改变主体的本质,不会改变情感的本质,不会改变商业的本质,不会改变信息的本质,但是技术会改变产生方式,从形式到效率,都会改变。这是过去两百年来的趋势,我相信以后还会持续,技术会带来越来越多对人的解放,包括对人性的尊重,因为人变成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一个竞争力;但是技术也会带来新的挑战和不定性。这个事情一直在发生,我们能选择的,是学习更好地让技术造福人类。
在谈技术对社会的重构之前,我想先谈一下数字革命与前几次技术革命的不同之处。数字技术引发变革最根本的原因是信息成本的大幅降低。按照摩尔定律,每隔一年半到两年,信息处理效率翻一倍同时成本减半。半个世纪过去,在摩尔定律的预言下,各行各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的非排他性——信息可以被无数人分享,它不像冰激凌,我吃了,你就不能吃了;石油我烧了,你就不能烧了。信息可以被所有的人分享和使用。信息成本指数级降低与非排他性叠加,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参与度。每个人都成为信息的贡献者、分享者、受益者、被影响者和影响者。我认为这是数字革命最根本的原因。
纵观人类历史,前几次技术革命都是自上而下的,是从最富有、最具权势的群体慢慢向其他阶层扩散,但数字革命不同。我们看到,普通甚至中下等收入的人正在成为数字技术最积极的使用者之一,这与传统的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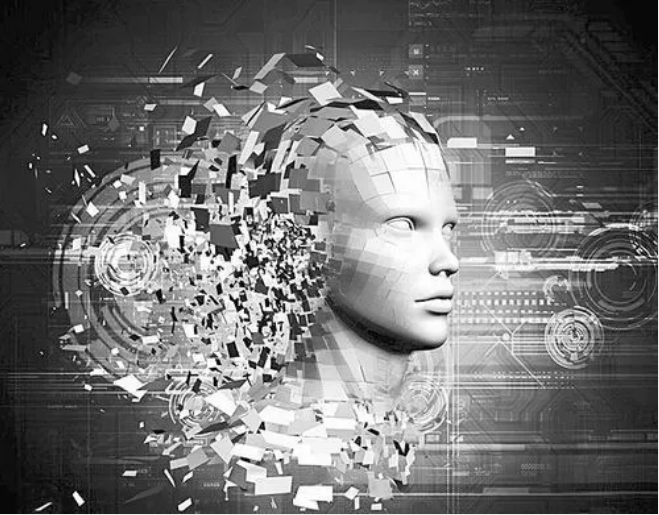
然而任何时候,新技术,特别是革命性技术诞生之初,人们都会有天然的抵御心理。一百多年前,中国在进行洋务运动、日本在明治维新。然而两个国家对技术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后来也因此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中国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思是技术只是一种工具。而日本是“全面西化”,甚至要“脱亚入欧”。历史证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不会因为接受技术就丢掉了民族性,反而闭关锁国,排斥新技术会带来更大的伤害。
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不仅仅停留在技术和商业上,我经常在思考:技术会在多大程度上重构我们的社会?

企业和组织要进行巨大的变革来适应。有的企业会发现远程办公效率更高,这种企业往往是目标导向,给员工更多的灵活性,同时也做了更多早期的转型准备。有的企业发现效率更低了,这跟组织自身的特点有关,也和其和数字技术的结合程度有关。
不但企业内部,企业和用户之间的关系也有巨大改变。在这段时间我看到很多企业的商业模式在发生改变,都在向网上迁徙,而且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以后完全线下的业务越来越少。有一位做零售的企业家告诉我,零售如果绝大部分业务在线下,即便现在仍然不错,也不代表未来的方向,不会投资了。

大半个世纪以前,经济学界有一场著名的辩论,是中心化的治理方式好?还是去中心化的治理方式更优。哈耶克的核心观点是,市场最核心的作用是把各种分散的信息能够整合在一起,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这个智慧的过程是中心化的治理方式无法替代的。
在观察疫情发展过程时,我经常想到哈耶克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在疫情中网络上有各种信息,有专家的,有政府的,有企业的,有民众的,就像一个市场一样,它把非常分散的信息聚合在一起。各方对这些信息不断吸收检索,直到找到认为合适的证据为止,这个过程就像信息的交易。但这个交易是有成本的,因为有些虚假信息需要过滤。这个时代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十几亿人投入参与的交流信息的场所。正面的地方是它会带来巨大的信息整合的价值,甚至在信息市场之上会产生一个思想市场。但它也会带来负面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降低虚假信息的外部性,要建立一个分辨和抵御假新闻的信息治理机制,帮我们更好的把信息分层。
第三个是重新定义人与技术的情感联系。有个寓言叫庄周梦蝶——我到底是在现实世界中还是虚拟世界中?这次事件给了我们一个比较极端的机会,技术一下子逼迫我们跟它们发生了更多联系,这会重新定义我们是虚拟的人还是一个现实中的人,以及我们对技术的情感联系。我曾经听到一个故事,因为疫情在家隔离,有人就会和自己的天猫精灵聊天,不是命令它去做什么,就是单纯的聊天。前一段时间,达摩院受一位失独母亲的邀请,用AI技术复原了故去女儿的声音来陪伴安慰这位母亲。罗汉堂还从心理学的角度评估了可行性。
如果没有数字技术,隔离中我们可能就买不到蔬菜水果,吃不到外卖,也看不到免费的《囧妈》。总而言之,疫情让很多人改变了对技术的态度和看法,从以前的不在乎甚至抵触,变成了接受甚至依赖。
当然也有不变的东西,我认为不变的是技术会继续解放人性。在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里面,技术与人结合的结果是人也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人必须像一个机器一样去跟机器配合,变成一个螺丝钉一样的东西,这是摩登时代里人的悲剧。后来出现的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也是把人当成工具,最大程度地压榨员工。梅奥的霍桑实验标志着人本主义崛起,此后企业家越来越意识到员工也是一种资本,一个企业的活力在于员工的创造力、一个企业的效率等同于员工协同的效率。另一方面,消费者越来越重要,生产是以消费者为核心来运作的。我们发现技术越进步,人类越解放。

下一页:张明 | 诡异的全球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