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颠覆性技术引发战术变革的规律
添加时间:2019-10-17 点击次数:1064
当今时代,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呈现多点突破、交叉融合、群体跃进态势,已成为推动新一轮军事变革浪潮的强力引擎。恩格斯曾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鉴于“技术决定战术”这一规律,考察颠覆性技术的演变轨迹,揭示颠覆性技术引发战术变革的规律,将为我军加快战术变革进程、引领战术理论前沿提供有力支撑。
以颠覆性技术为引领的军事技术是引发战术变革的决定性因素
颠覆性技术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的时代有与之相对应的颠覆性技术。分析战术变革的历史进程,在所有与战术变革相关的因素中,颠覆性技术和其物化的武器装备历来是战术领域最活跃、最具有生命力的因素,同时也是影响战术变革诸因素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以金属冶炼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出现和演变,先后产生了青铜兵器、铁兵器、骑兵格斗装具等代表性武器,促进了阵式战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火药制作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出现和演变,先后产生了火绳枪、燧发枪、后装线膛枪等火枪和火炮,形成了线式战术、纵队战术和散兵线战术。以动力机械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出现和演变,促进了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冶金业以及武器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机枪、坦克、飞机等新式武器,形成了以集群式散兵战术、梯次快速集群战术为主要标志的机械化条件下合同战术。以原子核反应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出现和演变,产生了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等核武器,形成了以“大纵深立体、空地一体”为主要特征的核武器条件下合同战术。以精确制导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出现和演变,产生了精确制导武器、新一代作战平台,以及高性能侦察器材、新型夜视器材、先进的电子战器材等一系列高技术武器装备,形成了以“精确性、立体性、机动性”为主要特征的高技术条件下合同战术。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出现和演变,产生了信息系统和信息化武器装备,形成了以“信息主导、网聚效能、整体联动”为主要特征的信息化条件下合同战术。
当前,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出现和演变,不断推动智能化、无人化武器装备和平台的创新发展和作战运用,武器平台之间实现自主快速交互,战斗力量基于需求实现动态编组,指挥人员依托战场全景式态势实施可视化指挥。随着人工智能由计算智能、感知智能向认知智能逐步迈进,智能化时代合同战术将由“人在回路中”向“人在回路外”转变,无人化、自主化、可视化特征更加凸显。
回顾战术发展历程,以金属冶炼技术、火药制作技术、动力机械技术、原子核反应技术、精确制导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犹如军事技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引领战术一次又一次的飞跃。

从武器和战术的发展历史上看,一种新武器最终取代旧武器而成为战场的主战装备,往往要经过一个其在武器系统中的数量比例及地位作用不断增长时期。当军事技术进步以量变的形式发生时,武器装备的发展比较平稳缓慢,因而对整个战术变革的影响不大。当新的颠覆性技术出现并产生能够改变战争总体面貌的新机理武器后,随着新式武器的广泛列装和实战运用而在战场上发挥主导作用时,战术体系就会被新质打破和替代。战术变革的历史过程正是在渐变与突变这两种发展形态的结合与交替中形成的。
在冷兵器时代,青铜、铁等金属兵器代替石器成为主战装备后,产生了阵式战术。在热兵器时代,单发火器数量种类的增加和质量性能的提升,产生了线式战术、纵队战术和散兵线战术。随着连发火器的出现,又驱使战术不断变革。机枪早在1883年就被美国的马克沁发明,并在1899年至1902年的英布战争中用于实战,但由于数量较少,并未引发战术的变革,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广泛运用才导致集群式散兵战术的形成。
1905年英国人发明了坦克。坦克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索姆河会战、康布雷会战中使用,并且取得了一定战绩,但是由于数量有限、性能不完善,只是作为步兵的支援武器,不可能成为主战装备,因而并未引发战术的变革,只是产生了机械化条件下合同战术的萌芽。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但坦克的打击、防护、机动和信息能力都有很大提升,而且重型、中型、轻型坦克也相继问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欧战场,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时,德军60个师中有9个装甲师。到1940年5月入侵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时,德军西线部队123师中,有9个机械化师和10个装甲师。坦克成建制的大规模集中使用,为梯次快速集群战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精确制导技术,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的激光和电视制导炸弹等精确制导武器仅占全部投掷弹药的0.2%。由于精确制导武器数量较少,以及打击精度和毁伤效能有限,因而并未引发战术的变革。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高技术的迅猛发展,一大批高技术武器先后装备部队,特别是精确制导武器运用更加广泛。1991年的海湾战争,多国部队共使用了13类82种精确制导武器,约占总投弹量的8.36%。以精确制导武器为基本火力的战略空袭、以精确制导武器为主要压制杀伤手段的空地反装甲联合作战和纵深打击成为多国部队迅速取胜的主要因素。以海湾战争为标志,高技术条件下合同战术已经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信息技术的兴起和迅速发展,驱使以信息系统为纽带的信息化武器装备逐步替代机械化武器装备而成为主战装备。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C4ISR系统网络化程度大大提高,基本实现了战场感知系统、指挥控制系统和作战行动系统之间的横向无缝连接。美陆、海、空军武器装备的信息化程度分别达到50%、60%和70%,空间系统超过70%,指挥控制系统超过80%。以伊拉克战争为标志,信息化条件下合同战术已经形成。
随着人工智能、移动互联、先进计算、智能交互、增材制造等颠覆性技术的群体涌现,产生了无人机、无人地面传感器、战斗机器人等无人化武器装备和平台,并采用“人-机”编组、以人为主的形式进行了实战运用。当前,无人化武器装备和平台的小规模使用,使智能化时代合同战术初现端倪。展望未来,当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不断发展完善,导致无人化武器装备和平台广泛运用,战斗编组由“以人为主”向“以机为主”转变时,才能引发战术的颠覆性变革,形成智能化时代合同战术。

从世界各国特别是中西方的战术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战术变革进程总是表现出一定的不同步性。究其原因,除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差异,以及战争实践的推动、作战环境的影响、战斗主体的认知等不同之外,颠覆性技术发展不平衡是主要原因。
以中西方战术变革比较为例,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代的社会生产技术水平明显高于西方,中国的铜、铁冶炼技术较为先进,冷兵器不但使用普遍,而且种类较多。而西方的铜器、铁器制作技术大多从西亚、东方流传过去,不仅制作工艺简单,而且种类也较少。在金属冶炼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下,中国古代阵式战术变革的步伐比西方要快。公元前541年“毁车以为行”的魏舒方阵,是我国步阵取代车阵的标志,像这样机动灵活、攻击能力很强的独立的步兵方阵,直到110年以后,以重装方阵著称于世的古希腊斯巴达步兵才接近于类似水平。步阵到骑阵的变革,我国在公元前2世纪至1世纪的汉匈战争中,步阵战术便逐渐让位于骑阵战术,而西方真正进入骑阵战术时代的标志,则是公元378年的阿德里雅堡战役。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战术变革的步伐开始落后于西方。虽然中国是世界上首先发明火药并首先使用火器的国家,但是到了元末明初,由于长期陷于发展迟缓状态的封建经济,金属管形火器的发展速度停滞下来。中国火器特别是管形火器从12世纪问世以来,经过长达800年的发展,直到19世纪中叶,与西方火器相比,仍然停留在前装、滑膛和火绳点火的阶段。西方在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推动下,各种自然科学门类逐渐确立与成熟完善,为生产技术的全面进步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也为近代火器的发展提供了源动力。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机器工业逐渐代替手工业,火器制作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西方各国加速对火器进行制造改进。这个时期,我国正处于腐败无能、闭关自守的清王朝统治之下,社会生产力仍然停留在封建手工业状态,枪炮制作技术反倒明显地落后于西方。在西方的线式战术、纵队战术和散兵线战术等新战术层出不穷时,中国还固守冷兵器密集阵形战术和骑射战术,从战术思想到具体行动方法都远远落后于西方。
到了现代,西方先后发明和改进了蒸汽机和内燃机,在以动力机械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强力推动下,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实践,机械化条件下合同战术已逐步成熟和完善,创立了比较系统的机械化战术理论。我军从创建以来,在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实践后,逐渐走上了诸兵种合同战术发展时期,机械化战术理论有了较大发展。但由于这个时期我军机械化工业技术和武器装备落后,机械化合同战术水平与西方相比差距较大。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原子核反应技术、精确制导技术、网络信息技术等颠覆性技术迅猛发展,先后形成了核武器条件下合同战术、高技术条件下合同战术和信息化条件下合同战术,经历了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战争实践,合同战术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相比之下,我军在上述颠覆性技术发展上始终处于“跟跑”追赶状态,虽然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推动了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合同战术理论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战术理论创新与实战运用上与西方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当前,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和群体跃进,为我军武器装备和战术理论创新发展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我国在近年来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文件中,已将颠覆性技术创新发展放在国家战略层面进行系统布局和预先谋划。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需求,我们要研判大势、超前部署、把握方向、抢占先机,尽早在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下大功夫和取得突破,实现我军技术和战术水平从跟跑向并行、领跑的战略性转变,使我军逐步成为智能化时代颠覆性技术和战术理论创新发展的领跑者和开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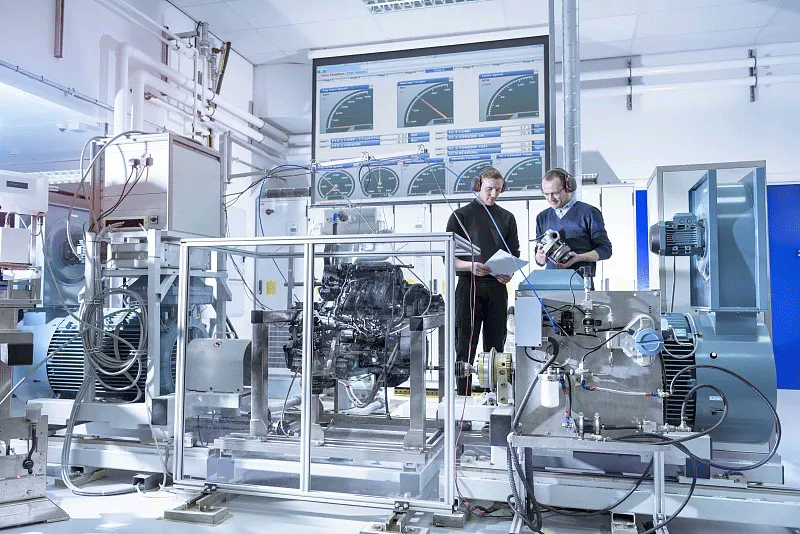
考察颠覆性技术和战术发展历史,可以发现,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水平是按阶梯式提高的,每一阶段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产生新的飞跃,形成新的技术或技术群,便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层次。每当新的颠覆性技术驱动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那么将引发战术新一轮的变革。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技术—武器—战术”是一个各要素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当战术与颠覆性技术、武器装备协调一致时,“技术—武器—战术”系统就处于某种稳态结构之中。只要颠覆性技术和武器装备不发生变化,战术就会表现为一种稳定状态,整个系统不再会有质的变化。战术在这种稳态结构中,虽然达到了高度的完美,但却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而不再向前发展。因此,为了使战术向更高层次运动,必须打破系统的稳定,研发新的颠覆性技术和武器装备,使系统达到一种新的稳态结构。就这样,稳态结构一次又一次的形成,而一次又一次的被打破,战术也就随之发生一次又一次的飞跃,从一个稳态结构进入另一个更高级的稳态结构。从世界范围看,颠覆性技术的发展速度加快,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就加速,战术变革的周期就相对较短;颠覆性技术的发展速度减慢,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就减速,战术变革的周期就相对较长。
在冷兵器时代,从公元前约3500年铜兵器开始出现,到铁器逐步替代铜器,再到中国北宋时期开始进入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代,历时近4500年。从公元前约3000年战车的出现,到铁器的运用促使步兵的兴起和战车的衰落,再到13世纪初中国的骑兵战术进入鼎盛时期,阵式战术从车阵、步阵到骑阵的变革历时达4200多年。
从10世纪初中国首次将火药应用于军事,到19世纪后半期单发火器逐渐成为主战装备,在经历了近1000年后,火器实现了从前装变后装、燃发变击发、滑膛变线膛、直把变弯托的转变。在冷兵器与火器的相交阶段,产生了方阵队形与疏开队形相结合的战术。随着火器的发展完善,从17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后期出现线式战术萌芽,到18世纪末纵队战术开始形成,再到19世纪中叶散兵线战术产生和20世纪初期趋于完善,单发火器时期的战术变革经历了约250年时间。
随着动力机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机械化武器装备登上了战争舞台并逐步成为主战装备。从19世纪80年代初连发武器出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坦克首次运用,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机枪、坦克、飞机的广泛运用,机械化武器装备从出现到成为主战装备历时约60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集群式散兵战术出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梯次快速集群战术产生和不断完善,机械化条件下合同战术变革历时约30年。
从20世纪70年代初美军在越南战争中开始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到20世纪90年代初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大量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再到21世纪初伊拉克战争中精确制导武器主导战场,历时约30年。高技术条件下合同战术从越南战争出现萌芽,到海湾战争已经形成,再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趋于完善,也历时约30年。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以信息系统为纽带的信息化武器装备逐步替代机械化武器装备成为主战装备。经过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的实践,以伊拉克战争为标志,信息化条件下合同战术已经形成。直到现在,信息化武器装备和其引发的信息化条件下合同战术仍在不断发展完善。
1956年人工智能被首次提出后,经过60多年的发展,虽然已经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催生了无人化武器装备和平台,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人工智能由计算智能、感知智能向认知智能发展征程中仍然存在诸多“瓶颈”问题。而突破这些“瓶颈”,依赖于计算机科学、数学、脑科学、心理学、语言学、逻辑学、生命科学等众多基础学科的研究攻关。当前,合同战术正处于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时期,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发展速度,决定了无人化武器装备和平台主导战场的时间,也决定了新一轮战术变革的周期长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的颠覆性技术发展速度有快有慢,颠覆性技术转化为新一代武器装备,进而引发战术变革的时间有长有短。总的来看,颠覆性技术的发展速度快慢与战术变革的周期长短具有相对一致性,即“快”导致“短”、“慢”导致“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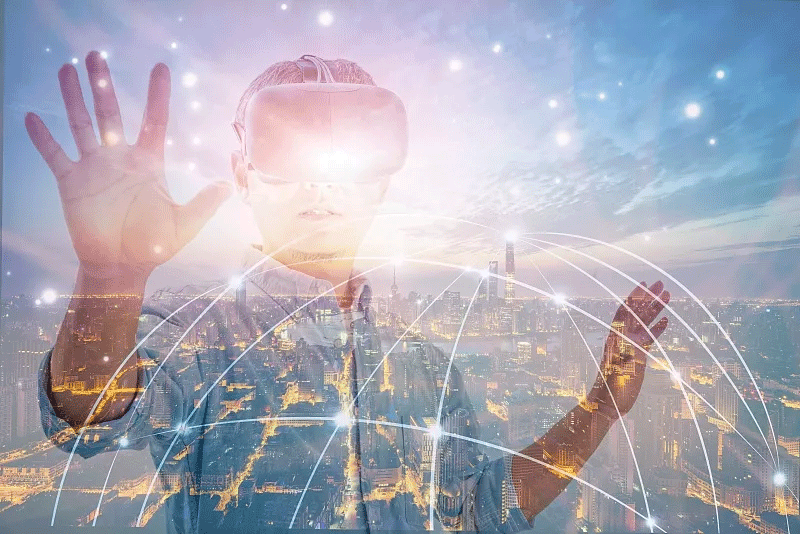
回顾颠覆性技术发展和战术变革历史,从控制论的角度看,在“技术—武器—战术”系统中,颠覆性技术通过主导武器的发展方向来决定战术的变革走向;战术变革通过对武器的选择来对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提出需求。技术决定战术,而战术又对技术有反馈作用,这也说明了技术和战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关系。
战术对技术的反馈作用,通常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事后”选择,即战术对现有技术转化后的武器装备进行选择,而不是被动接受;另一个是提前“预定”,即着眼战术的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对未来技术和武器的发展提出预先的需求。
对于“事后”选择,战术对技术和武器的发展有着严格的选择性,而不是技术和武器的奴仆。不符合战术发展规律的技术和武器,最终会被排除在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随着火药制作和动力机械等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德国人曾制造了一种威力巨大的火炮——“巴黎大炮”。这种大型火炮口径210毫米,身管长34米,弹重120千克。“巴黎大炮”全重约750吨,需要用50节火车车皮分别运载,到达目的地要用龙门吊车组装后,才能发射炮弹。“巴黎大炮”尽管在当时火力威猛,但由于体型笨重、不便机动,射速太慢、反应迟钝,目标庞大、易遭攻击等原因,后来被战术无情地淘汰了。考察战术变革历史,可以发现,战术史包含着战术对技术和武器选择的整个过程,现在列装的武器都是经过实践检验后由战术精心选择保留下来的。
对于提前“预定”,要以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为基础。因为科学技术越发达,生产各种各样武器的可能性就越大,战术就可先在理论上按照它的要求去选择,而不必让那些不适应战争需要的武器生产、装备部队之后,再用血的代价去选择了。在古代,由于科学技术水平十分低下,人们生产出的武器种类非常少,战术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只有生产什么武器就拿过来打什么仗。到了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十分发达,人们可以通过技术途径把某些设想变为现实,生产出不同功能和种类的武器。由于武器的选择余地变大了,人们可以根据战术发展的规律,来提前设计武器和提出技术需求。战术对技术的这种反馈作用,当人们的认识正确的时候,就会使技术和武器沿着战术发展的轨迹而演变;当人们的认识错误的时候,就有可能使技术的发展和武器的制造背离战术发展的规律。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前苏军的骑兵将领们错误估计了未来战争的情形,认为应当用小坦克来代替一部分骑兵。这种错误观点造成的后果是前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拥有大量的不能适应战争的小坦克。由于这些小坦克火力威力小、装甲防护性能差,既不能代替骑兵中的战马,也构成不了坦克兵的基础,使前苏军在大战初期就遭遇惨败。这一惨痛的教训,应该引起我们反思。
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战术变革对颠覆性技术发展的反馈作用越来越强、力度越来越大。从智能化时代合同战术“无人化、自主化、可视化”典型特征看,“无人化”要求智能化、无人化武器装备和平台能够代替人类执行作战任务,实现作战力量由“以人为主”向“以机为主”转变,这对人工智能、增材制造、新材料等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提出了需求;“自主化”要求无人系统能够像人类一样拥有智慧,实现自主感知态势、自主决策规划、自主控制协调、自主评估效果等自主能力,这对深度学习、移动互联、智能交互等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提出了需求;“可视化”要求实现作战全流程全要素的可视化,使指挥人员能够在“后台”实施全景式的可视化指挥,这对传感器、物联网、量子通信、先进计算等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提出了需求。
在战术对技术的反馈过程中,我们要高度关注战术对技术的提前“预定”。通过周密论证、科学预测,尽可能增加“正能量”的反馈作用力,减少“负能量”的反馈作用力,从而更好地选择未来的武器,确立未来的战术,设计未来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