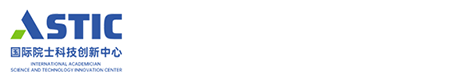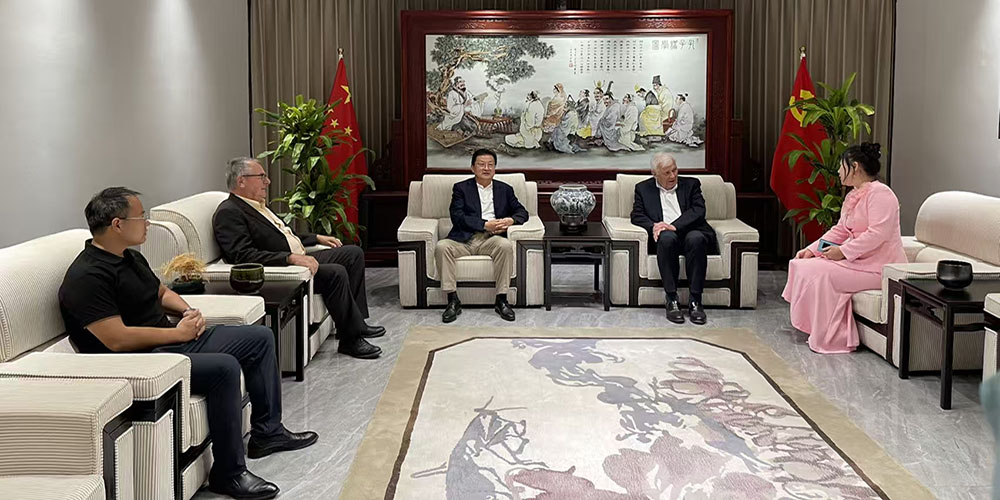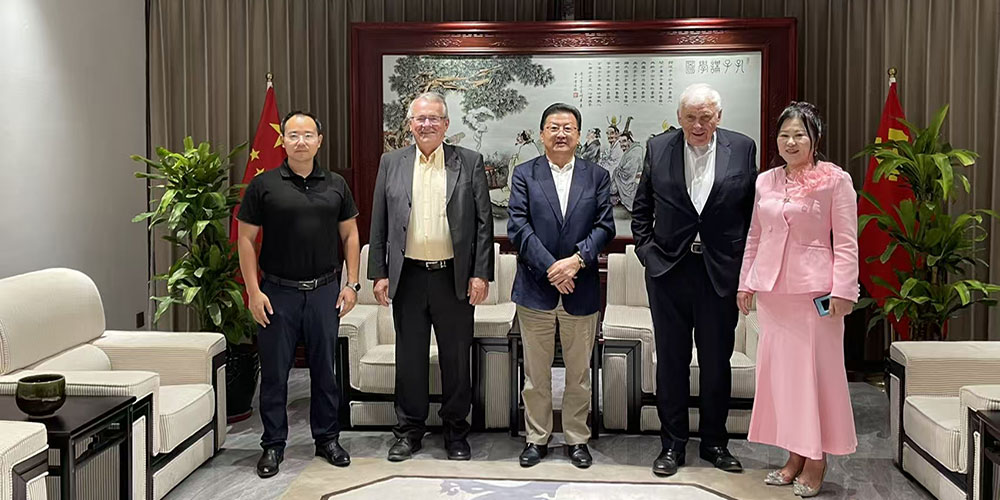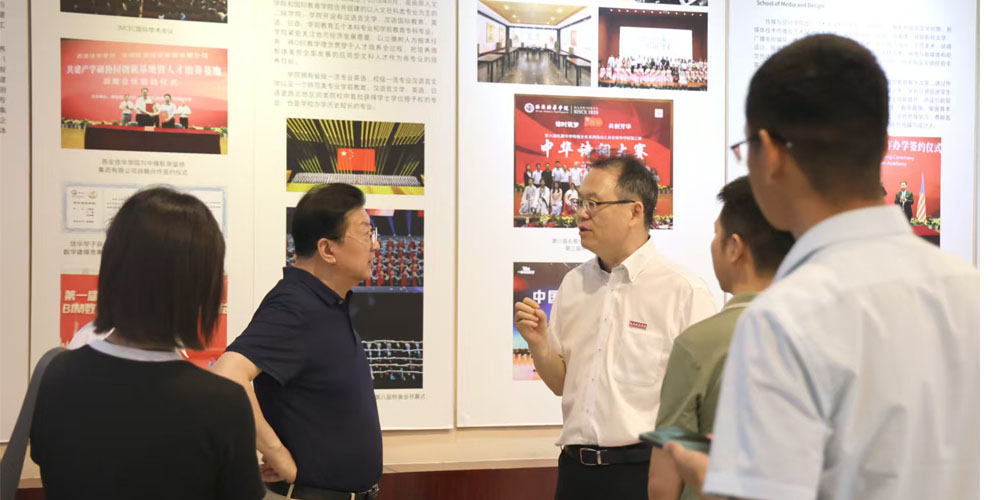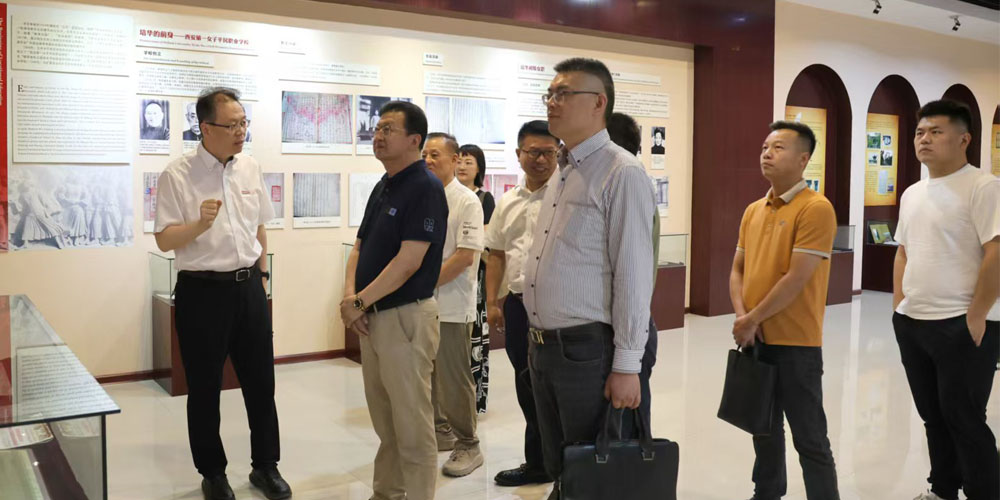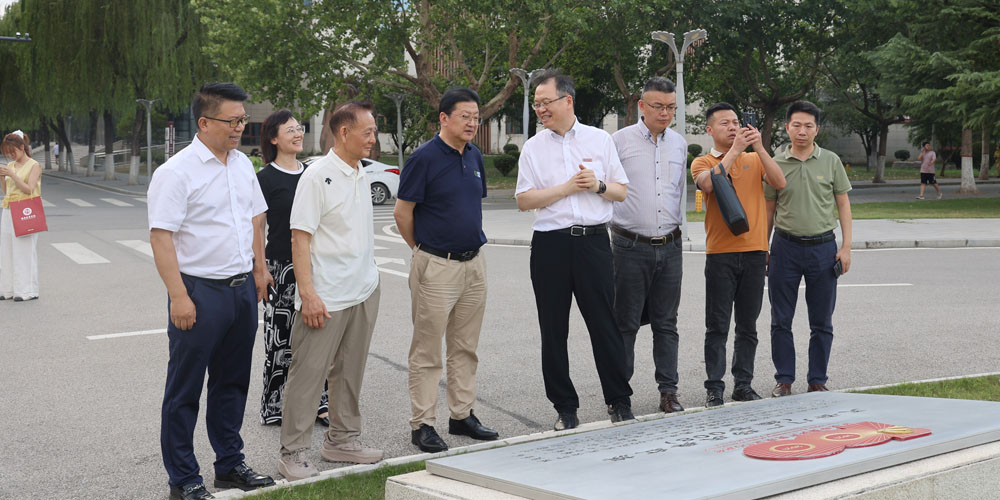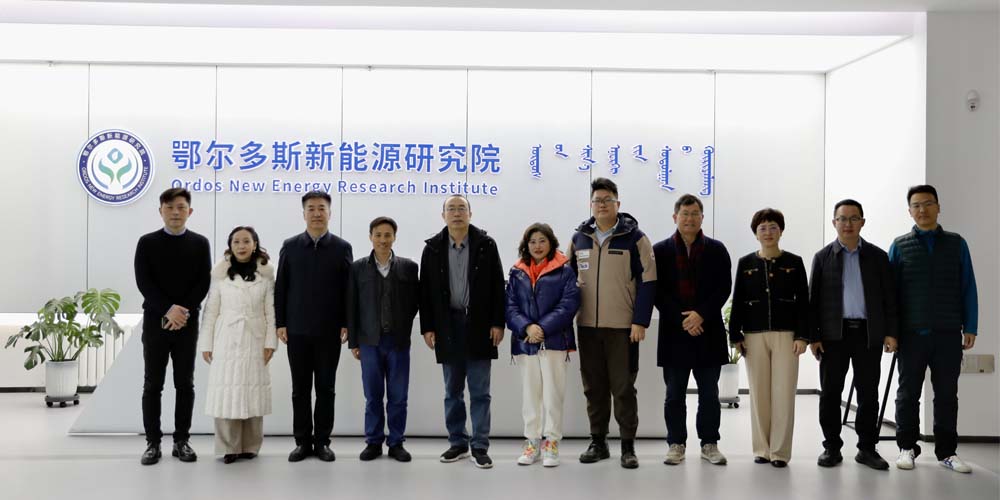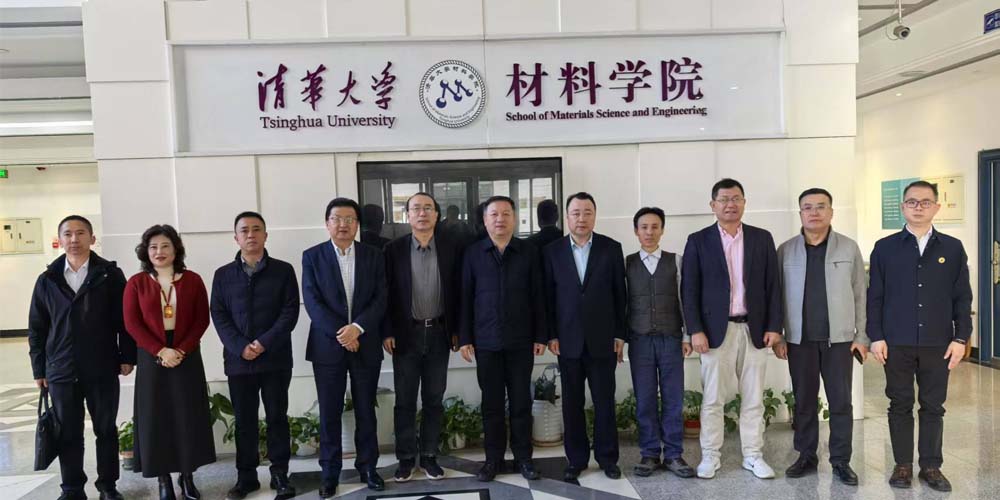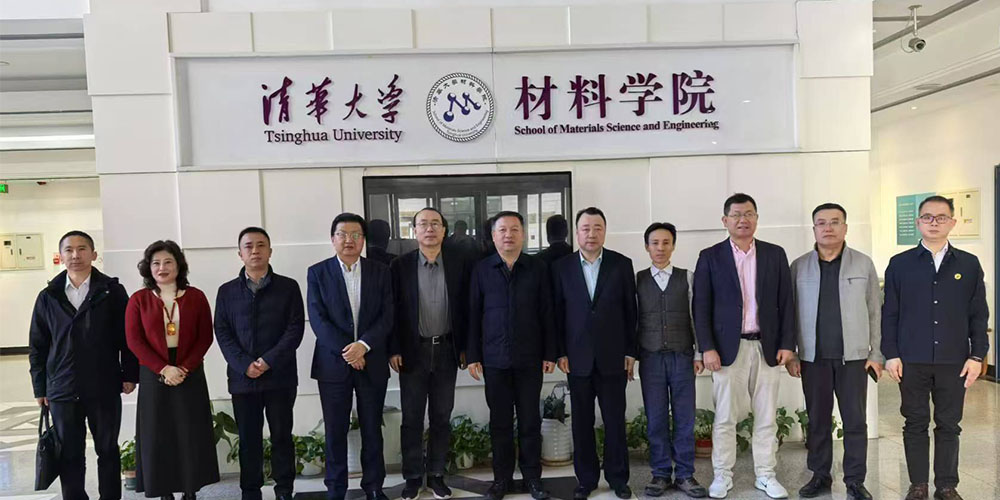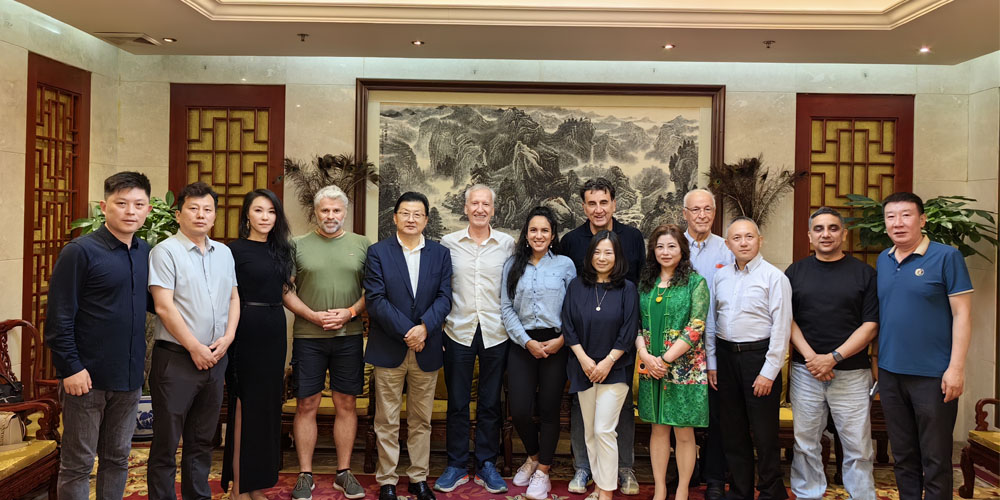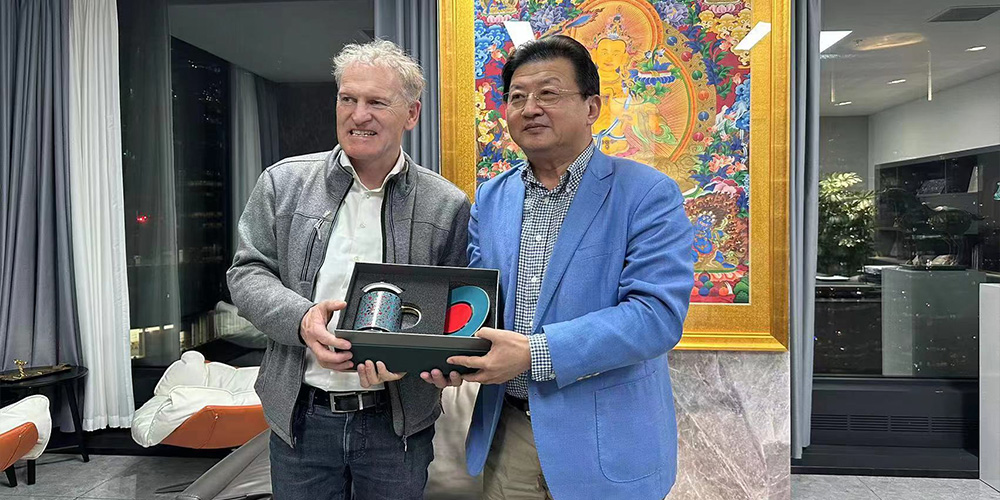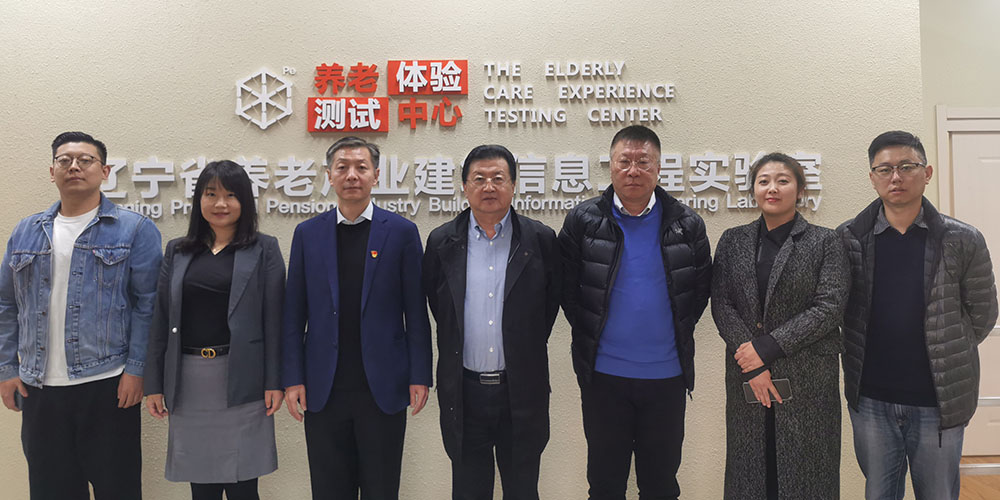浏览次数:480 发布时间:2022-06-30 10:05:06
当前,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拟在中美间建立一种以科技为核心的新型大国竞争范式。中美两国的这场世纪竞争,不仅考验两国的科技战略制定能力,更考验两国的科技战略执行能力。
一、美科技政策决策咨询体系基本构成
美国科技政策决策体系遵循《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体制,分为行政系统和立法系统,两个系统分工协作。美国总统掌握行政权力,拥有国家科技活动的最高决策权和领导权。国会拥有立法权力,科技立法草案、科技决策机构设置、重要科技官员任命以及科技预算等都需要通过国会参、众两院审议和批准。
美国行政系统科技体制基本框架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最高协调机构是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和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此外,有6个主要部门和机构组成资助体系:国防部、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宇航局、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农业部。
NSTC具有内阁地位,为总统服务,跨行政部门协调科学技术政策的决策,确保总统目标的贯彻和执行。
OSTP就与科学和技术有关的所有事项向总统和总统办公厅提供建议;与联邦政府各部门和机构以及国会合作制定科技政策,帮助联邦政府各职能部门和机构落实总统承诺及优先领域。2021年,拜登任命生物学家埃里克·兰德(Eric Lander)为OSTP主任,并兼任首席技术官。2022年2月,兰德辞职,迄今首席技术官仍处于空缺中。
PCAST成员由总统任命,多是“在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有不同见解和专长的非政府成员”,主要负责“涉及科学、技术和创新的政策事项”,并就涉及科技事项向总统提供咨询意见。报告和信函是PCAST为总统提供建议的官方机制,通常由小组撰写,并由PCAST整体批准。自老布什政府以来,PCAST职责还包括两个不同的法定咨询小组职能。2004年,PCAST被指定为国家纳米技术顾问小组,审查国家纳米技术倡议,并向总统和NSTC提出建议。2005年,PCAST被指示承担总统创新和技术咨询委员会职责。拜登政府PCAST共有30位成员,是来自于天体物理学和农业、生物化学和计算机工程、生态学、免疫学和纳米技术、神经科学、网络安全、国家安全等领域专家,其中包括20位美国国家学院成员、5位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2位前总统内阁大臣和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
机构 |
职能 |
构成及成员 |
|
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 |
PCAST与总统关系密切,响应总统、副总统和NSTC的请求,提供有关联邦计划的反馈,并就具有国家重要性的科学和技术问题积极向NSTC提供建议。 |
成立于1990年,成员是总统任命的杰出人士,来自工业,教育和研究机构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平均每年举行四次公开会议。理事会成员没有任期限制。 |
|
国家科技委员会(NSTC) |
内阁级,为总统服务,负责协调大规模的跨部门科技计划,确保总统目标的贯彻和执行。 |
成员由副总统,OSTP主任,具有重大科学和技术责任的内阁秘书和机构负责人以及其他白宫办公室负责人组成。工作由六个主要委员会组织:科技企业,环境,国土与国家安全,科学,语义学教育,科技,还包括两个特别委员会:研究环境联合委员会,人工智能特别委员会。 |
|
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 |
就与科学和技术有关的所有事项向总统和总统办公厅提供建议;与联邦政府各部门和机构以及国会合作制定科技政策;OSTP与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就联邦研究发展向总统提供建议预算。 |
自1976年以来,白宫S&T政策制定和咨询机制一直由OSTP管理。由主任办公室和六个核心政策团队组成:气候与环境,能源,健康与生命科学,国家安全,科学与社会,以及美国首席技术官。 |
表 美国主要决策咨询机构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是美国独立联邦机构,是美国最重要的科学决策机构之一,它的中长期科学研究投资方向将影响全球科学发展。在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许多领域,NSF是联邦政府支持资金拨付的重要渠道。2022财年,NSF年度预算88亿美元,提供资金约占联邦政府基础研究支持资金的25%。
经过长时间运行积累,美科技政策体系已形成一套成熟的运行规则。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归总统管辖,同时又与国会联系紧密,一方面受国会监督和制约,另一方面,国会也给予行政部门一定立法权的委托。行政部门关键职位在执行法律过程中也有相当大的自主裁量权。因此,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时,行政官员往往被视为联接国会和资本的关键纽带。业界将其总结为一种美国政治的“铁三角”决策模式,即由国会委员会或者小组委员会、行政部门相关管理机构的职业官僚和相关利益集团组成三方决策集团。
二、近年对组织机构的调整
近年来,美国历届政府不断加强对科技发展的重视,并对其组织体系构建进行深刻而低调的调整,优化关键机构,促进其战略执行。
一是创设新职位。2009年,时任总统奥巴马创设首席技术官职位,并任命维吉尼亚州的技术部长阿尼什·乔普拉为首任官员,同时领导OSTP。此举被分析人士称为美国政府本世纪最好的创新之一,充分彰显了科技在美国内政外交政策中的重要地位。2021年,拜登上任后再次创新,将首席技术官地位提升至内阁级别。此外,2021年,拜登政府还首设了国家网络总监职位,统筹美国数字防御战略的制订和落实。
二是聚焦新问题增设新政府机构。国务院增设下属新机构“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CDP),帮助“解决网络和新兴技术的外交问题”,并确保将价值观“纳入美国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推进能持续支撑美国价值观的数字技术愿景”。2022年6月,拜登提名内特·菲克(Nate Fick)为大使,领导CDP。据悉,菲克履历中有网络安全公司、新美国安全中心从业经历,对北约战备、印太外交都有涉猎。该机构和人员设置充分突出了拜登政府推进网络空间外交的政策取向。
在2022财年综合拨款法案中,拜登正式宣布投入10亿美元用于创建新机构卫生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H)。2022年5月底,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宣布正式启动ARPA-H,由马里兰大学情报与安全应用研究实验室首席科学家Adam H.Russell担任代理副主任。ARPA-H作为NIH的独立实体,领导“高风险,高回报的生物医学和健康研究”。HHS声称,成立该机构是拜登“为支持美国开展雄心勃勃、且可能具有变革性的卫生研究而做出的新努力”。
三是加强在人工智能和量子等重点领域的决策咨询机构。例如,人工智能方面,2018年,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2021年,商务部成立人工智能咨询委员会;2022年,人工智能咨询委员会成立五个工作组。为避免美国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落后,美国众议院议员建议成立“技术竞争力”委员会,由副总统哈里斯领导,并且提议设立负责技术竞争力的总统助理办公室,制定国家技术战略及调整政策和预算重点等。量子技术方面,2020年,成立量子计划咨询委员会;2022年,拜登签署一项总统行政令,将量子计划咨询委员会直接置于白宫权力之下。此外,美国防部建立新兴能力政策办公室(Emerging Capabilities Policy Office),负责为国防部研究和采办人员制定与人工智能、高超声速等新能力有关的政策,帮助将新能力整合到国防部的战略、规划指南和预算流程中,以加快新兴能力的部署。
三、未来调整方向
未来,美国政府为强化与中国科技竞争能力,或将继续对联邦政府机构和运行机制做出调整。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就此提出建议:
一是支持商务部。CNAS认为,商务部当前职能无法支撑其执行不断扩大的使命,应根据财政部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办公室的模式进行重组;指定商务部为美国情报界成员,提高政府对执行国家技术战略所需的经济,贸易和技术发展进行分析的能力;建立信息融合中心,使商务部能更好地了解国内外的工业和技术趋势;扩大利用现有的工业调查机构。对特定行业定期调查;下设立国防生产法“第三章”办公室,监督与经济或技术竞争力有关的非军事项目。国会应确保向商务部分配足够的财政和人力资源。
二是更新立法和法规,应对新的供应链和技术转让风险。国会和行政部门应编纂和定制信息和通信技术及服务行政命令13873,法律应授权商务部长审查、授予或阻止外国实体在美国销售信息和通信技术及服务的许可证;更新《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伯曼修正案,解决数据隐私和间谍威胁;为联邦研发资金接受者制定最低网络和人员安全标准和要求;制定国家数据保护和隐私法。
三是简化技术政策协调和实施。技术政策决策的责任分散在一系列政府部门和机构中。国会和白宫需要合作,确保建立有效的机构间机制来协调和实施技术政策。建立技术安全协调小组(TSCG);创建一个框架和机制来制定优先决策;指定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工业与分析办公室作为联邦政府外国公司风险信息中心;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内建立国家经济技术安全情报中心,主要职能应包括集中和汇总与外国产业基础脆弱性相关的情报,跟踪国外新兴技术发展,建立国外供应链和经济依赖性的“地图”。
四是建立专门机构启动、维护和扩大与盟国和其他志同道合国家的协作技术关系。国会应在国务院设立技术合作办公室,该办公室由一名技术部助理部长领导,将成为管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技术伙伴关系的主要美国政府实体。
四、科技决策体系存在制约
国家技术战略的制定和落地,不仅需要远见卓识,更需要落地流程和体系,并逾越实施中的官僚主义、法律和监管障碍。从这点来说,无论未来怎样调整,美国体制和官僚体系具有的一些原生特点,是其科技战略落地无法规避的掣肘。
一是政策连续性难以保证。美联邦政府已形成成熟运作的官僚机制,新的治理体系架构很难打破既有模式,尤其是以总统行政令形式形成的政策,未落实到立法层面,其连续性和稳定性如何尚难定论。美国总统任期四年一届,上任两年后,总统内政外交政策往往要向有利于中期选举倾斜,其政策很容易追求形式,力求短期震慑效应。例如,美新成立的“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目前成员职业履历大多为外交出身,使“网络空间治理”沦为美外交工具。
二是政策效率难以保障。美三权分立的制度设定,使得一些重大政策落地程序繁琐,政策出台既受总统管辖,又受国会制约。同时,参众两院议员代表各自不同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中都从自身角度出发,需要双方不断协商、互相妥协,一来过程耗时,二来政策出台时可能已变形。例如,美为遏华力推的《创新与竞争法案》,参众两院法案之间部分重叠议题存在明显的愿景差异。虽然两院都同意授权国家科学基金会大幅提高支出额度,但在优先事项上有显著差异。参议院版本法案提出,5年内投资290亿美元加强美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等尖端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拨款100亿美元建立20所区域技术中心;众议院版本则更注重应对气候变化、环境可持续性以及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提出5年内拨款133亿美元解决以上问题,拨款70亿美元建立10余所区域技术中心。参众两院分歧导致法案进展缓慢,影响了拜登政府战略目标的落实。例如,6月底,英特尔宣布,因《芯片法案》仍具不确定性,补贴难以到位,原定在俄亥俄州建设的芯片工厂将无限期停止开工。
此外,美官僚机构规模庞大,且兼具复杂性和分散性,导致一些重要机构职能弱化。例如,OSTP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战略领导作用,而是扮演技术顾问角色;经济部门与国家安全机构运行割裂,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实际运营中更侧重军事与外交,而对技术与经贸关注较少,影响其在涉及技术创新、经济治国等安全决策中的作用。
三是科技巨头影响较难平衡。当前,美国科技巨头壮大为富可敌国的非国家行为体。根据2022年4月28日数据,以苹果、亚马逊、谷歌为代表的美国头部科技公司合计市值超过5.56万亿美元,每一家公司市值都超过了荷兰、瑞士、西班牙等国2021年GDP总量。在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形成高度赋能的当下,技术已经成为影响政治博弈、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达到这种体量的科技巨头,对美内政外交政策的影响难以简单估量。透视美当前针对科技巨头政策,充分显示出拜登政府面对科技巨头时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拜登政府试图强化对大型科技公司反垄断调查,在一些关键岗位任命以反科技巨头著称的相关人士负责反垄断工作;另一方面,美又希望能够纳入科技巨头力量,在地缘竞争中为己所用。拜登政府对继任兰德的首席技术官划定的条件,再次透露了这种既用又防的心态。据悉,白宫希望首席技术官候选人有深厚技术知识、熟悉硅谷生态系统,以便使科技公司在美科技体系中发挥最大效力;又不希望首席技术官候选人和其家庭与科技巨头有利益关联。这导致首席技术官一职长期空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科技战略的制定和推进。
结语
当前,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拟在中美间建立一种以科技为核心的新型大国竞争范式。中美两国的这场世纪竞争,不仅考验两国的科技战略制定能力,更考验两国的科技战略执行能力。为应对竞争,无论美国,还是中国,不仅要制定出目标愿景明确的科技战略,更需要构建联通学术界、工业界的组织流程和政策执行体系,方能用好政策杠杆,提升国家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实力,赢得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