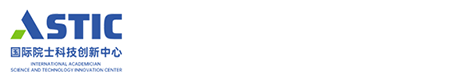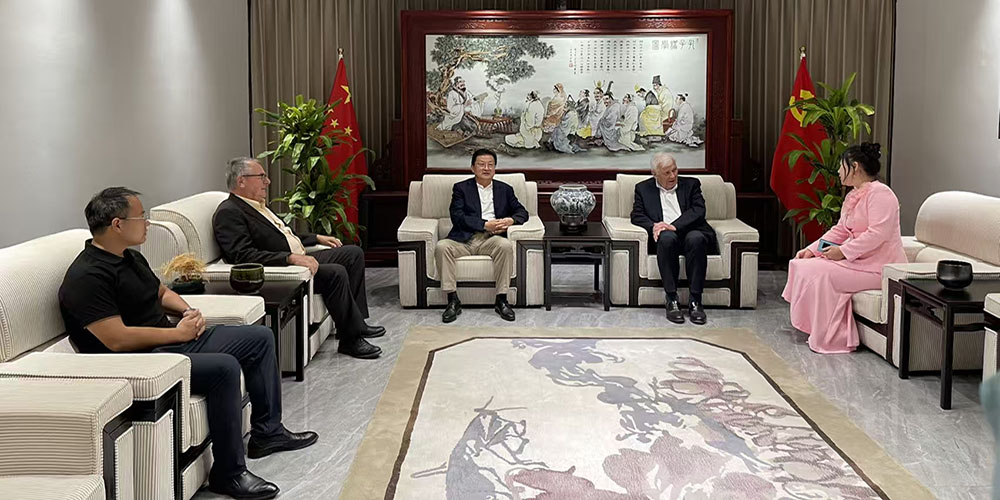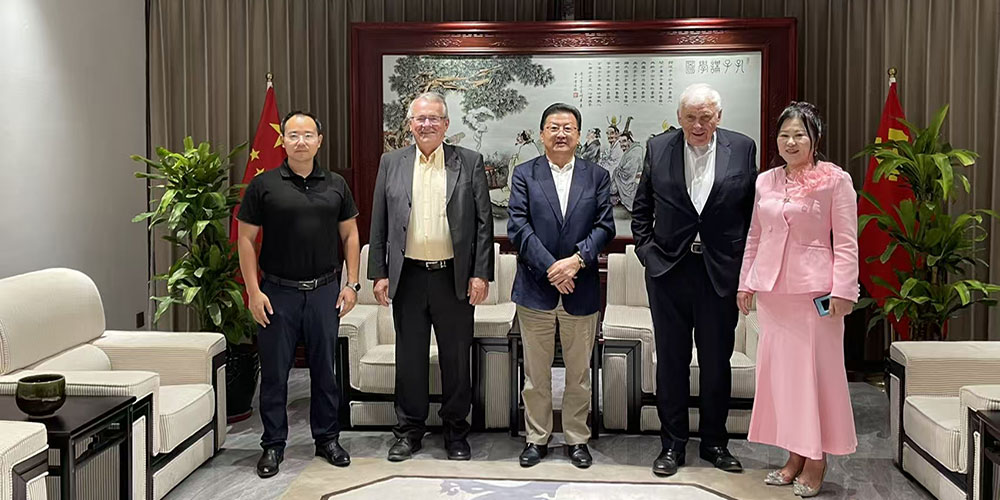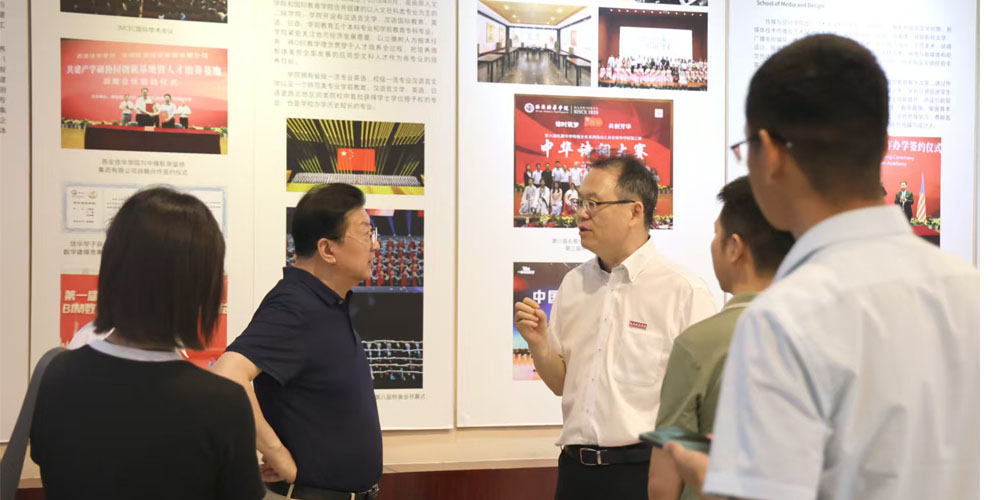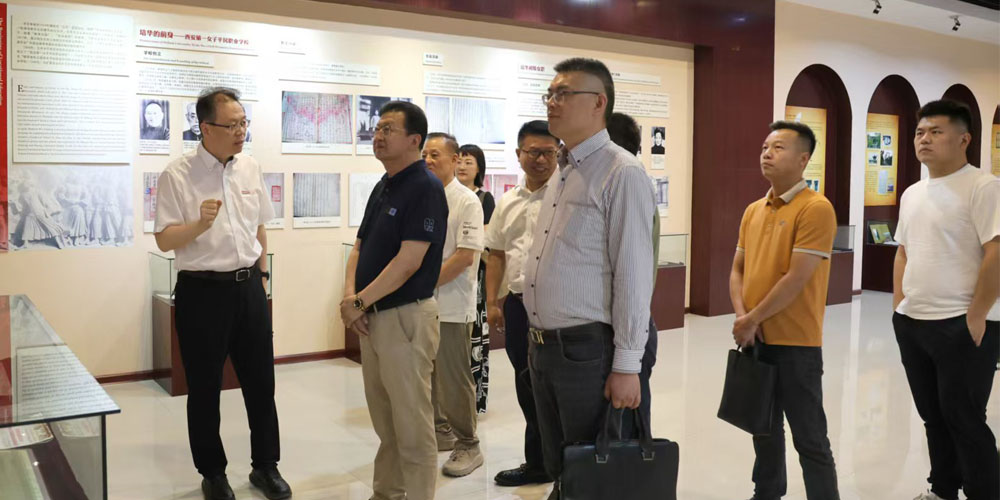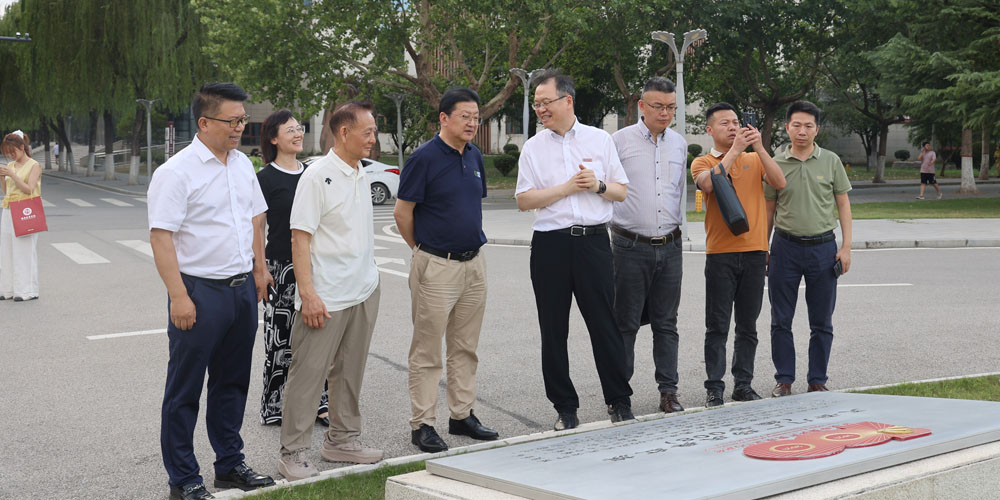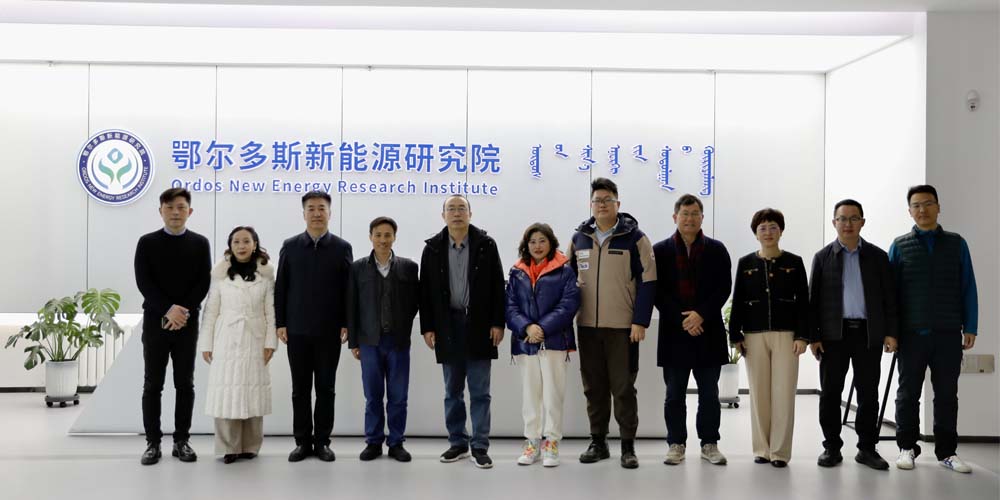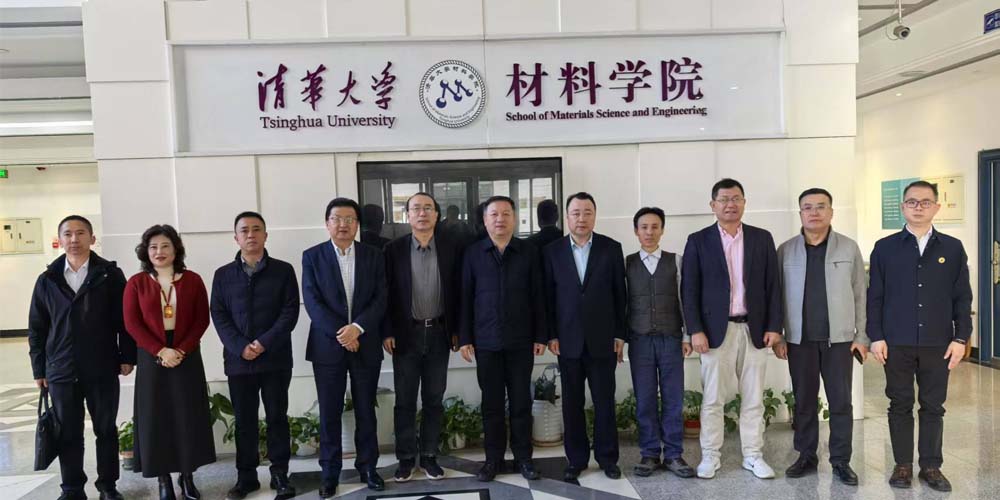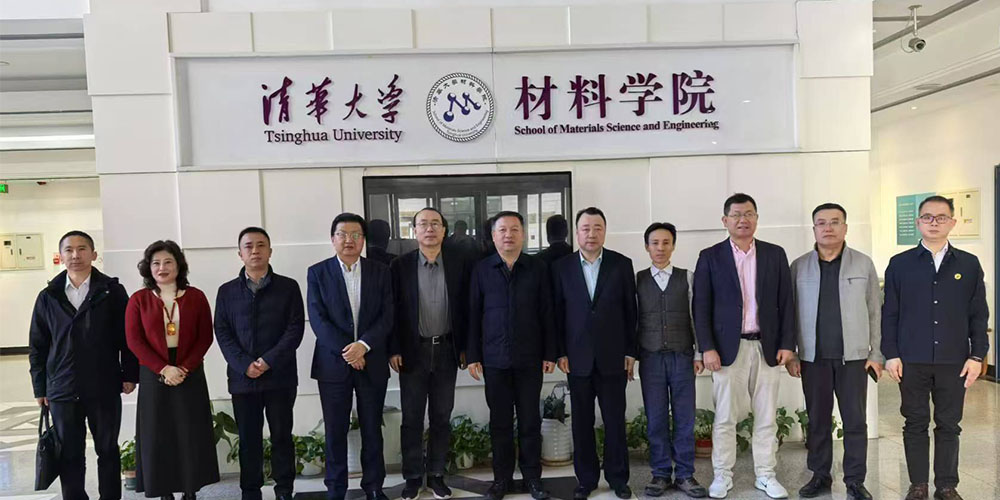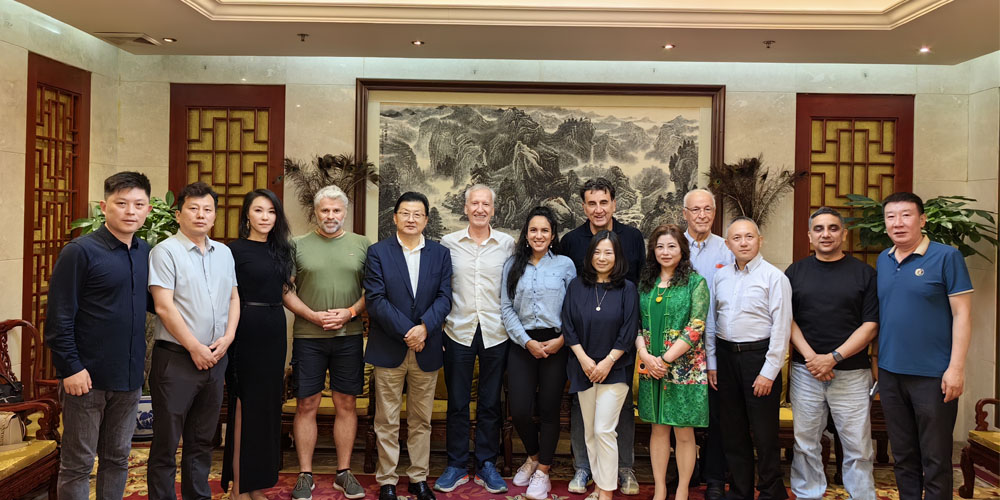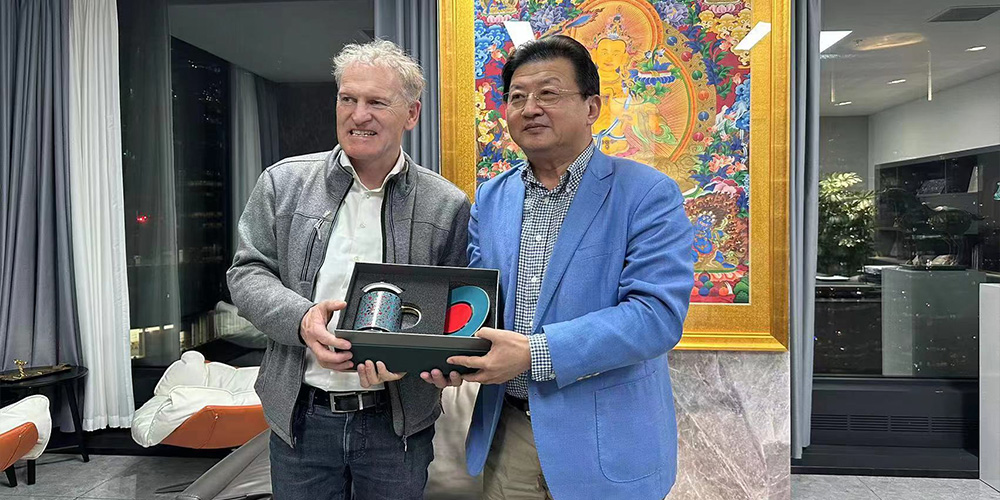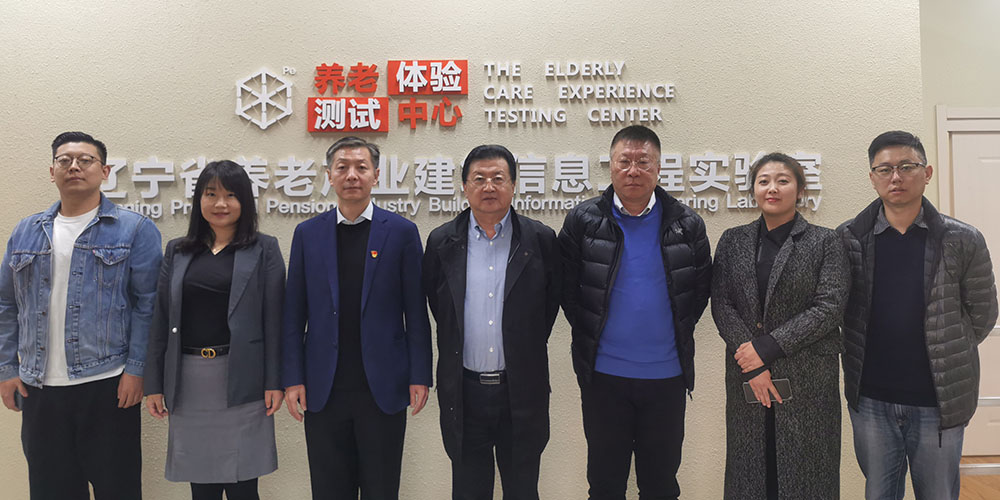浏览次数:592 发布时间:2022-12-26 09:12:45
前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亨廷顿在预言文明的冲突时,并未预见到今天的俄乌冲突,也未研究过科技进步对文明冲突的影响。
俄乌冲突本质上是俄西冲突,即俄罗斯传统帝国文明以新欧亚主义的面目与西方文明发生的一场大规模冲突。这场冲突很可能会以俄罗斯的国力衰竭和国家失败而告终。俄罗斯未来的命运要么像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要么会成为大号的伊朗。
俄乌战争再一次凸显文明冲突中的文明实力的较量结果,这个较量自二战开始,到冷战结束,以及后来的伊拉克战争和反恐战争,都是以胜负悬殊的方式结束冲突。而导致胜负悬殊的实力,既不是能源储量,也不是传统军事力量(包括传统核力量),而是具有降维打击能力的科技实力。这个实力会具体体现在强大的军事、经济与金融手段上,我们称之为国家新实力——不依赖资源与人口数量,而依赖创新驱动的经济与军事实力。
通过已发生的历史可以预见,决定文明冲突结局的不是政治和宗教,而是产生科技进步的文化与制度,以及相应的国家治理能力。
简言之,科技实力决定了文明冲突的结局:或彼此相融、或势均对峙、或一决胜负。无论何种结局,都取决于各类文明内部的创新驱动力。因此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在后俄乌战争时期(Post Russia-Ukraine War),国家新实力主义的创新驱动战略在高度竞争的复杂国际环境中改革与升级的方法与路径。
1.文明的冲突与科技进步
亨廷顿(1927—2008)曾在其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预言,“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他认为,后冷战时代最主要的冲突是在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穆斯林和亚洲社会将会与西方文明产生最为严重的冲突。
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很快印证了亨氏的预言,使得他的著作和理论在全世界广泛流传。
特朗普在就任美国总统不久后,就开启了中美贸易战和联合西方对华的高科技封锁,更进一步验证了这个预言。
从已发生的文明冲突的历史来看,随着基地组织和其他极端宗教组织被消灭,原本高昂的反美和反西方情绪在伊斯兰世界快速降温。多数伊斯兰国家对西方文明都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态度。
这种态度,背后是文明实力较量后的结果。如果没有海湾战争和后来的反恐战争显示出悬殊的力量对比,两种文明的冲突是不会那么容易平息下来的。因为无论是战争较量,经济与金融较量,这两种文明的实力都不在一个水平上。
因此,所有冲突结束后都会出现一种新的平衡,即,主导文明与非主导文明和平共处,彼此不再成为对方的威胁。所谓主导文明就是科技实力强大的文明。这也并非是两种文明势均力敌的结果,而是主导文明对非主导文明的威胁能力“去势”后的平衡。
美国对中国发动的高科技封锁,实质上就是针对强大竞争对手的 “去势”操作。
因此,亨廷顿在分析文明的冲突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考量——文明的实力。亨廷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它仅仅将文明的冲突聚焦在宗教与政治层面,而忽略了影响文明实力的科技进步因素。
从上世纪冷战至今,每当西方在发现其他文明对其构成威胁时,都会内部一致地采取“去威胁”的操作。而最大的威胁来自科技竞争。因此,在高科技上禁止向对手或潜在威胁国出口,已成为西方的一种类似科技北约式的操作。这种操作在《瓦森纳协定》基础上形成了西方国家内部密切分工与协作的科技共同体,演化出一个“合众科技帝国”(United Technology Empire,UTE)。我们把这个正在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 “合众科技帝国”形态称之为“科技帝国”。未来文明的冲突将也将是“科技帝国”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冲突的领域将更多集中于科技疆域,而非地缘疆域。
我们对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做一个补丁:
文明的冲突取决于冲突各方的科技实力及其背后的创新能力。各文明之间如果不能彼此包容和共存而发生冲突或对立,必然会产生三种结果:第一是一方对另一方降维打击,使其“去势”和边缘化;第二是保持均势平衡的全面冷战;第三种就是高强度科技竞争下,彼此克制冲突的半融合状态,即竞合状态。
李光耀曾在1994年说过:“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在30或40年的时间内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
可以预见,在“后俄乌战争时期”,全球化不会解体,但会以部分脱钩的形式,进入到“脱钩性全球化”(Decoupled Globalization)状态。这种状态会出现层级分明的竞合关系,即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科技与军事合作会比以往更加密切,与西方文明接近的国家次之,与西方文明对立但可部分相融,且不挑战其地位的国家会被部分脱钩(脱钩程度取决于对立与共融的程度),而与西方文明敌对且构成威胁的国家会全部脱钩。
2.创新驱动动力
既然文明的冲突,尤其是破坏性的冲突会止于势力均衡的结果,国家新实力主义必然会成为冲突各方,尤其是相对弱势一方的主要国家战略。因为一国的军事、经济与金融实力的核心就是该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这个能力虽然自一战以后也一直被各大国高度重视,但因为各国创新模式与动力产生机制不同,最终出现了实力悬殊的结果。比如二战以后美国与欧洲差距的形成,冷战后美苏之间差距的形成。
如果我们把创新驱动的模式(战略模式、制度环境、以及相应的国家治理能力等)比作“创新驱动引擎”,大国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这个引擎技术先进性的竞争。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近一百年来,人类进入到了一个财富大爆炸(The Great Enrichment)的时代,这是一个从数千年漫长的物质短缺时代到“供给过剩”时代的历史跃迁。有很多对这个现象的解释,但其根本原因是科技进步,也正是科技进步产生了现代经济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
比如科技进步产生了人类史上最大的经济共同体——全球供应链,这个覆盖全球经济总量90%以上国家的跨域经济共同体,大大提高了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共同福祉,从而降低了共同体成员之间战争的可能性。
既然科技进步影响着文明冲突的结局和历史演进的方向,那么我们就要思考产生科技进步背后的动力是什么?我们总结工业革命后的历史,把科技进步的动力总结为商业需求、军事需求,基于前二者的军民两用需求,以及人类高阶内在需求的“2plus+1”模式。
商业需求——工业革命后,激烈的市场竞争推动企业不断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资本追逐回报率的商业需求就成为技术发明与改进的动力。因此,商业需求是创新驱动的第一动力。
军事需求——从大航海时代开始所有帝国的扩张与征服,都离不开航海技术和坚船利炮。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军备竞赛,都显示出科技实力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底层逻辑。军事强国都在以举国之力来发展军事技术,因此,军事需求对技术进步的推动力与产出效率不仅远高于商业动力,而且还对技术发展趋势产生重要影响,比如航空、航天、计算机、互联网与GPS等技术,都是军事应用先于商业,随后应用于商业,并带来商业繁荣的。可以说,军事驱动为创新驱动的第二动力。
军民两用——尽管世界军事强国都会采取举国体制,在研发上可以不计成本,但这些投入也都是对本国国力的消耗,如果军事科技不能转化为商用,商用技术也不能转化为军用,军备投入与扩张就会导致国力衰竭和军力下降。而军事技术的商业化,不仅会带来经济繁荣与国力上升,反过来还会推动军事技术的持续进步。同时。成熟的商业技术应用于军工领域,可以大大降低军事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军备成本。比如商业机器人、AI与星链,及其背后的半导体芯片技术会推动战场无人化和海陆空天一体化的军事技术进步。因此,军民两用技术就形成了前述的“第一动力”和“第二动力”的融合,这个融合动力并非是一个新的动力,而是对两者的升级。
马斯洛需求塔尖的高阶需求
除了上述两大动力及其融合动力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驱动力,我们称之为“第三动力”的内在驱动力,就是人类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即无需外在利益驱动的自我实现动力。人类文明的进步,最根本的推动力是人的探索、发现、发明和创造的内在驱动力。这个驱动力是产生伟大哲学思想、艺术作品、科学发现和重大发明创造的源泉。
第三动力非常类似于中国道家哲学“三生万物”的含义。因为只有这个动力才是人类探索无限、创造万物的本源动力。
历史上几乎所有科学发现与发明都非出自纯粹的商业目的,包括瓦特的蒸汽机与莱特兄弟的飞机发明,以及贝尔实验室产生的大量发明。多数发明都是发明家们内在的兴趣驱动,而产生这类兴趣需求的马斯洛需求塔尖的社会文化、制度环境则是一个国家能够持续推动科技进步,并产生颠覆式创新的生态体系,没有这个生态体系,光靠钱是砸不出伟大发现与发明创造的。
3.突出竞争特征的新型举国体制
俄乌战争标志着地缘帝国时代的结束,未来国家间的主要竞争将集中在科技“无尽的前沿”领域,开疆拓土,争夺控制权。比如美国就会通过这个竞争来获得经济上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高价值端的霸主地位,在军事上获得压倒性的战争主导地位。
这个趋势也将产生代替地缘帝国的新型帝国形态——科技帝国。
中国与这个帝国间的关系并非是完全脱钩与对立冲突的关系,而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竞合关系。在成熟的高科技领域(主要是军事应用领域),美国限制中国获取相应的敏感技术,而在非敏感领域,美国是以特别301条款来约束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也就是说,凡是特别301条款涉及的技术和产品,只要遵守WTO规则和国际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这类交易与合作是不受限制的。在关键技术领域,如果中国换道超车,能够自主发明创造出新的技术,就会形成新的知识产权疆域和边界,突破美国对高科技的封锁。这完全取决于中国的独创能力。
因此,未来世界文明间和大国间的主流竞争,将越来越表现在科技疆域的“领土之争”上。这种竞争将以发现、发明、创造和创新为开拓和征服力量,形成以知识产权为领土边界和防御力量的大国间竞争格局。
因此,在俄乌战争后的复杂国际环境中,国家创新战略的重点就是要突出国际竞争,包括创新制度环境、创新动力机制,以及国内人才培养和国际人才吸引等方面的竞争。一定要避免重蹈冷战时期苏联举国体制完败美国的覆辙。
举国体制是自二战以来大国间科技竞争的主要方式,并非苏联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的独有。美国二战时期的大量军事援助与曼哈顿计划,以及后来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都是举国体制。然而,举国体制的方法与路径不同,结果也会大相径庭。如何提升中国的国家创新竞争力就要研究新型举国体制的模式与机制。既然美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强大对手,就要对标研究它的举国体制模式,以找到能与之抗衡且适合中国新型举国体制的改革之路。
首先,在举国体制的中美竞争上,中国拥有比美国更大的资源优势,比如政府对科研的投入,以及万亿政府引导基金向技术资本转型上,中国的优势远超美国。然而,在科研的投入产出效率上,中国又远远落后于美国,这也是政府不敢在基础研发上的投入下重注的深层次原因。此外,在对早期科创企业的投资上,美国的“硅谷+VC+大学+纳斯达克”模式吸引了全球的科技风险投资,而中国的政府引导基金与数万亿PE股权资本一样,都拥却挤在“IPO窄路”上,追捧那些业绩进入增长阶段的企业,而将早期高科技企业拒之门外。由于投早、投小、投专精特新的专业难度较大、风险较高,让很多资本望而止步。那些以财务业绩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考核标准的政府引导基金,根本无法发挥引导作用。这就使得举国体制下的国家资本无法形成与美国的技术资本抗衡的竞争能力。
在科研资金使用和科研资源的分配上,我们也一直存在很多误区,就是一切向体制内的科研机构倾斜,这个误区是导致我们的科研投入产出比远远低于竞争对手的重要因素。而美国在军工领域的举国体制,其基本原则就是以军事需求为引领,以市场竞争为机制,给获胜者生路和优厚的奖励。
比如,1972年美国空军原型机项目办公室公布了“轻量级战斗机”(Lightweight Fighter, LWF)计划。项目对招标者提出的要求是需要一款具备高机动性的战斗机,同时强调重点是降低重量和成本。LWF计划并没有承诺实际进行生产,但为了在成本控制方面美国空军设定了一个每架飞机的离厂价格不高于300万美元的目标(按照1972年的美元币值计算)。整个这一切是按照美国国会所坚持的“先飞再买”(fly-before-buy)的采购方式。这种方式是客户(即国家或军方)对市场竞争机制的充分运用。
五家主要的承包商参与到了LWF项目的竞逐当中。这五家公司分别是:波音公司、通用动力公司、凌-特姆科-沃特公司(LTV)、洛克希德公司和诺斯罗普公司。1972年4月,美国空军最终选中了两家获胜者:通用动力公司和诺斯罗普公司。
美国国防部DARPA的市场机制运用更加明显。其举国体制的三大特征就是①国家出钱。②汇聚全国顶级创新资源。③赛道竞争,优胜劣汰。DARPA的科研项目管理是市场化和专业化的项目经理制。其在高风险的前沿科技领域高概率成功的秘诀,就是汇聚顶级研发创新资源(研发团队靠谱),并在他们中间进行竞赛和择优选用
可以看出,美国军工领域的举国体制,颇有罗马斗兽场的残酷性。那些参与空军投标的飞机制造商,一旦落标,前期投入也付之东流。但正是这种竞争机制,才确保了美军的军力世界领先的地位。
而相比之下,我国的举国体制,却没有完全走出苏联模式,具体表现为资源分配与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依然以权力运作模式为主。权力运作模式会远离市场竞争,脱离需求导向。这不仅会导致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有重蹈苏联覆辙的风险,还会滋生新的腐败土壤。比如近期国家半导体大基金的腐败问题,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缺少竞争机制会让中国原本超过美国的举国资源优势无法发挥出来。
因此,中国的创新驱动战略与举国体制,就要从与美国这个强大对手展开全面竞争的角度,进行制度改革与模式创新。两国之间不仅仅是在具体科技领域的资金投入与人力资源的竞争,而是在创新驱动的动力机制与创新环境的制度设计上的全面竞争。
4.具有竞争属性的战略的架构
我们把新驱动战略的架构分为四大基础和三大支柱:
四大基础——科学发现(Discovery),原理发明(Invention),体系创造(Creation),技术创新(Innovation),简称“双发双创”,英文缩写DICI。
三大支柱——人才(Intellectual)、资本(Capital)、创新环境(Environment),英文缩写ICE。
四大基础的概念和相互关系,迄今为止十分混乱,概念语义大都是约定俗成的用法。这会对战略架构的设计会产生误导。厘清四大领域的边界与相互关系,对国家资源、市场资源、国际资源的有效配置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科学发现(Discovery)——指的是人类对未知领域的科学探索与发现
发现未必会带来发明与创新。人类的大量探索未必会产生有商业价值的技术,比如天体物理学、量子物理学等。但是科学发现是技术创新可以持续和找到方向的基础。在科学发现中,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发现与后来的技术发明和创新关系最为密切,而达尔文的研究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物理学与技术发明几乎无关。
(2)原理发明(Invention)——指的是从未有过的新技术或新方法的产生
发明的出现,有可能是科学发现导致的,也有可能与科学发现无关。比如瓦特、爱迪生和莱特兄弟等许多发明,并非因为他们对科学理论懂多少。科学上的很多发现都是在发明之后才出现的。比如火药的发明早于化学理论的出现;莱特兄弟的飞机发明,也早于空气动力学理论的出现。
(3)体系创造(Creation)——指的是利用已有技术原理或方法产生的全新的体系,由此产生了对人类有重要影响的技术方向和产业趋势
很多创造都是基于已有发明原理上的体系化构建,创造意味着新体系和新趋势的出现。比如汽车发动机,就是在蒸汽机发明原理上的创造。发明未必会产生趋势,但创造一定会产生产业的趋势。我们常常说“发明创造”,把发明和创造连在一起,就是人类的一些重大发明后来通过创造,形成了久远的发展趋势,比如电动汽车就是一项产生趋势的创造,但不是发明。因为电动汽车的汽车和电池技术原理都已存在。马斯克的火箭发射与回收,星链等技术都属于基于已有技术的全新创造,而非发明。
(4)技术创新(Innovation)——指的是在发明和创造基础上的持续的改进与升级
创新特指能够创造价值的技术革新与突破。相比发明创造,创新是一种高频次的实践活动,与创造相比,创新更强调的是在细分或超细分领域对系统性能的持续提升与改进,而创造更多体现的是对已有技术聚合所产生的新技术体系和发展趋势,比如光刻机是一项重大的发明和创造,在这个体系迄今还没有被其他技术替代,而所有向更小尺寸芯片的技术进步都是创新,而非发明和创造。
“创新”一词在中文语义中非常能够表达科技进步的实质。“创”有颠覆性或破坏性(对传统体系破坏)的含义,即英语里的Destructive,所谓“不破不立”,也有突破原有疆域的含义,即英语里的Breakthrough。“新”就是无中生有的新方法和在前沿领域开辟出新疆域的含义。我们习惯上往往把新创造和创新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