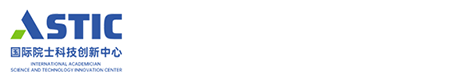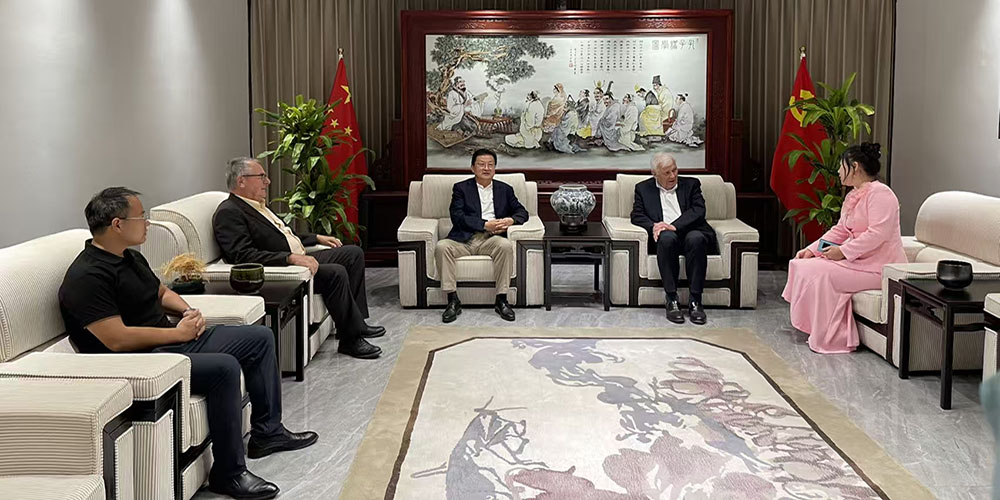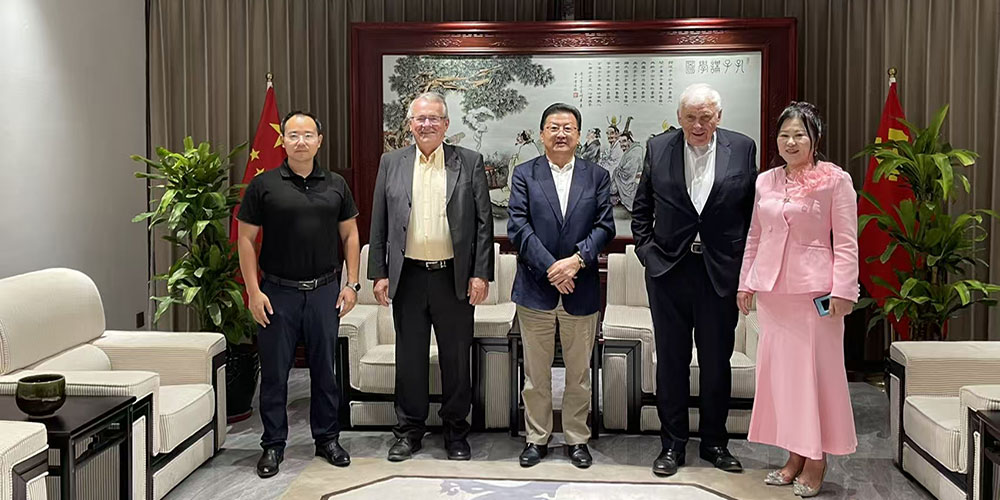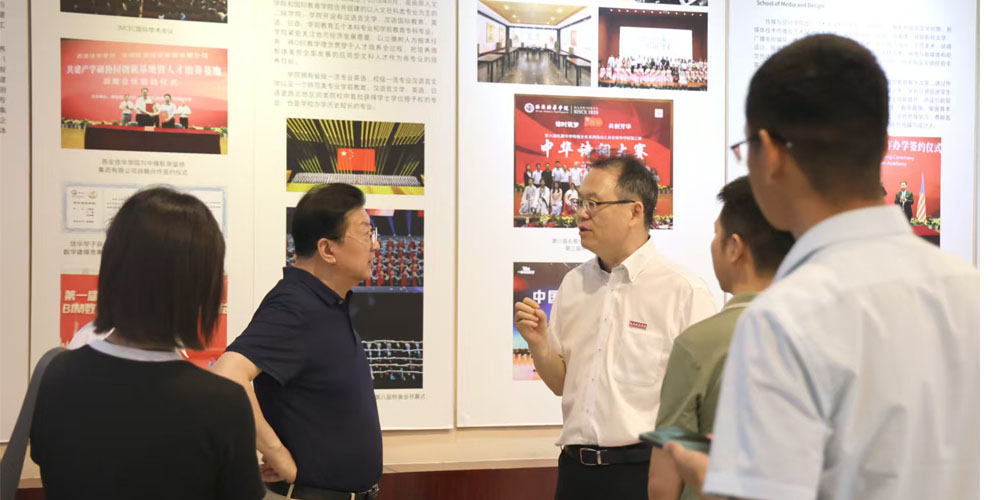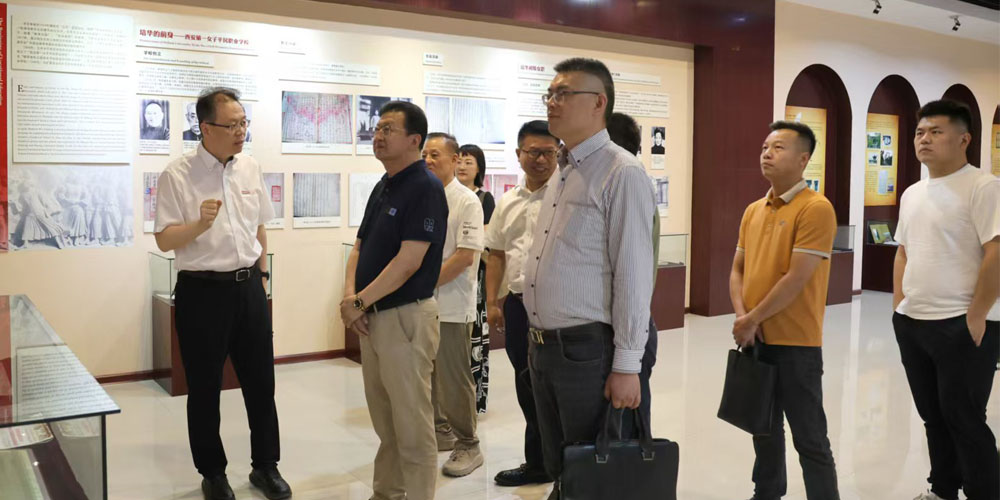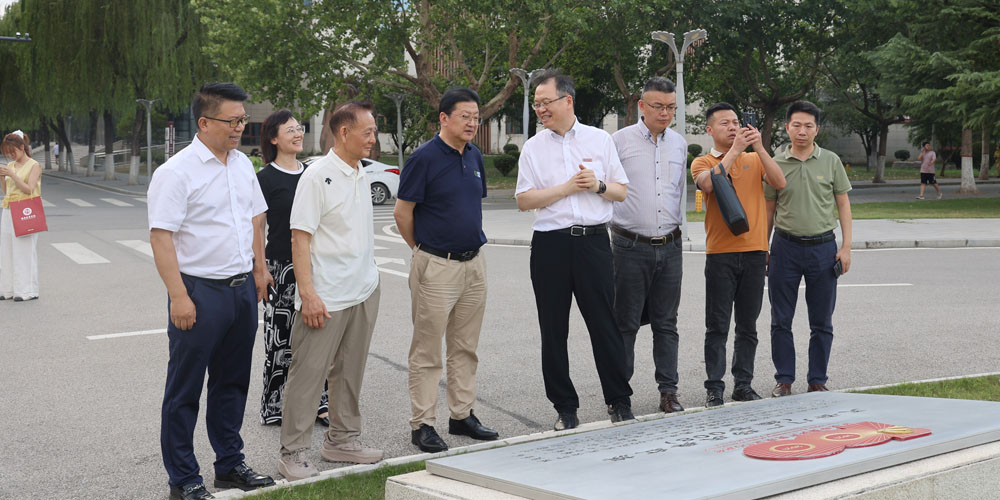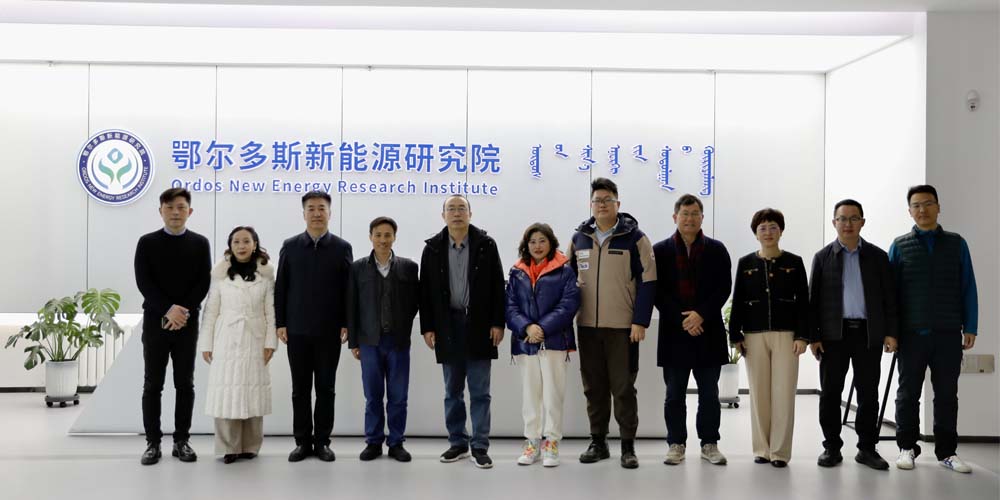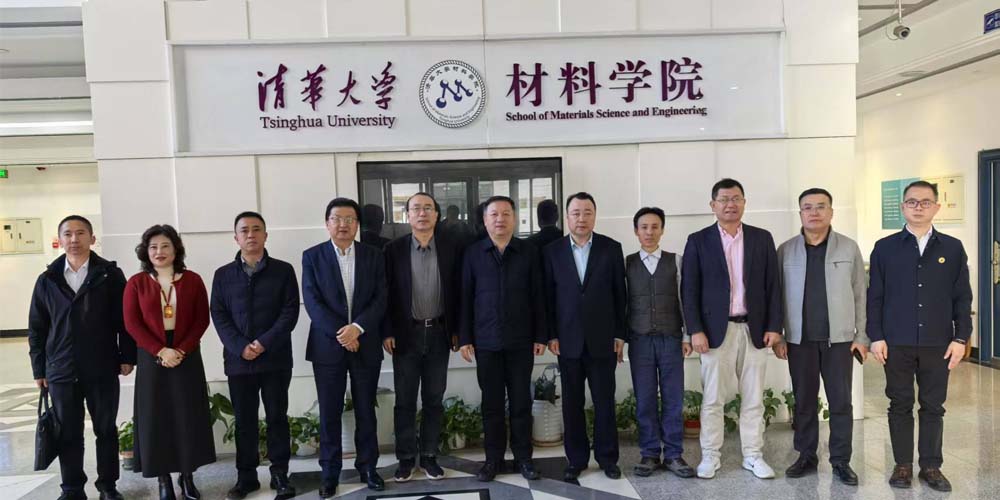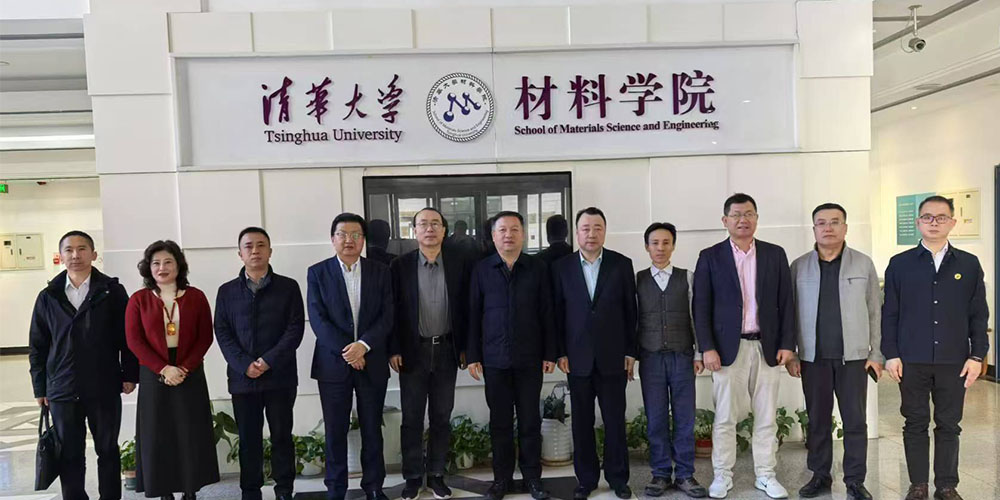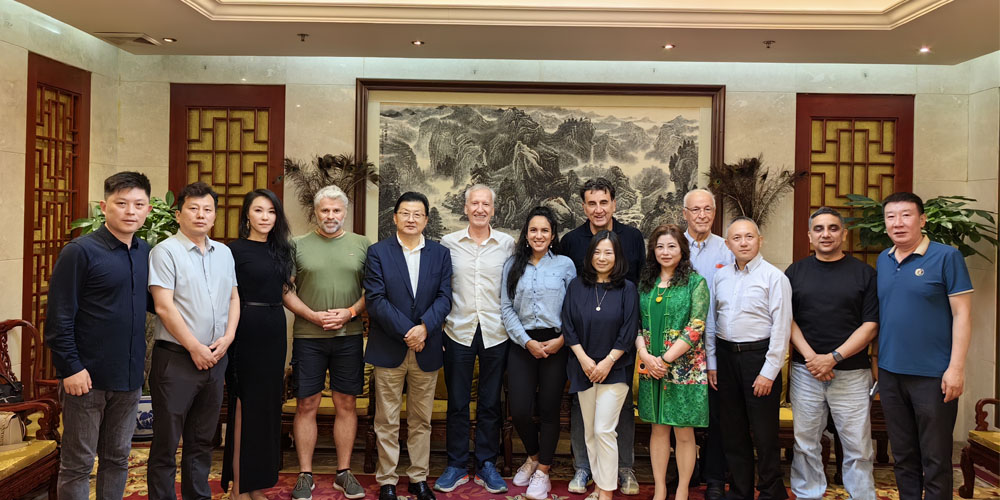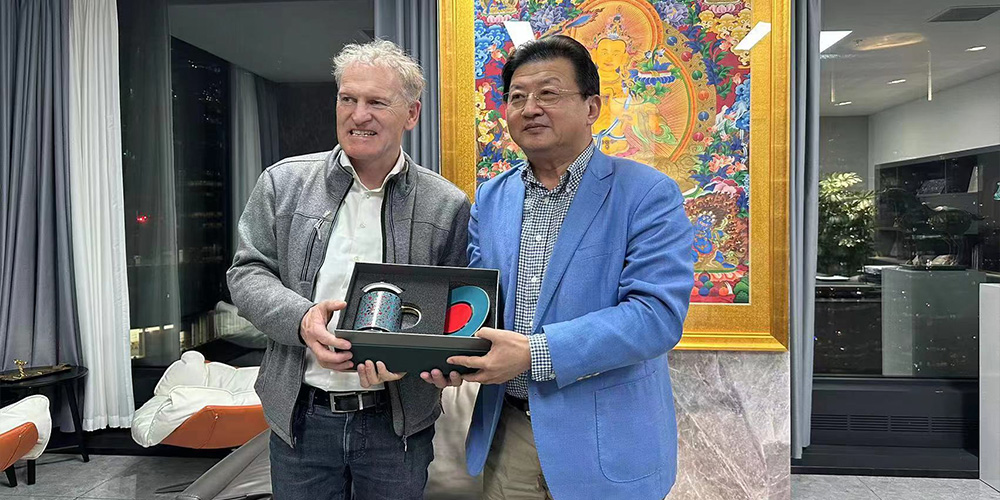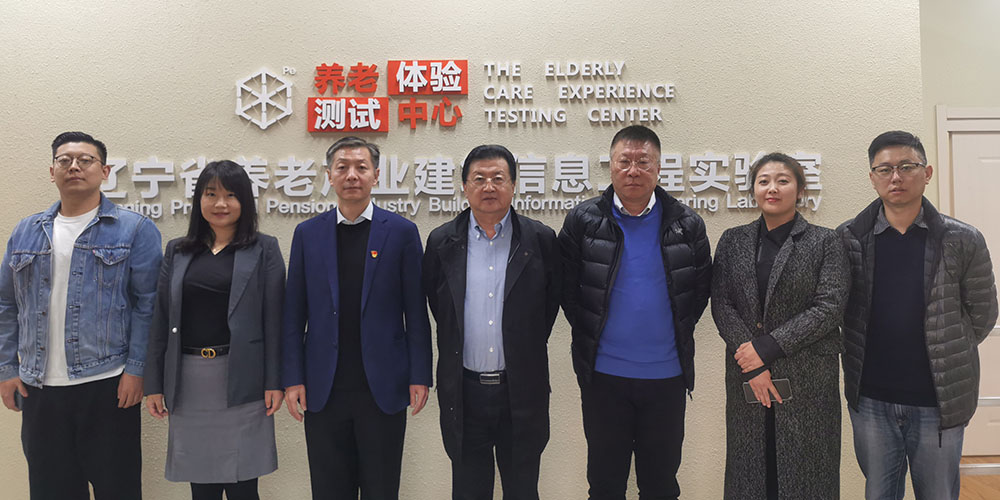浏览次数:705 发布时间:2021-03-16 08:05:17
产业结构概念的泛化和滥用已经严重削弱了结构性分析在发展问题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现代产业体系概念在继承了经典产业结构研究中的长期性、内生性和动态性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针对传统产业结构研究的基本假设和主要命题与变化了的典型事实之间日益严重的冲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拓展:一是在经济结构分析中引入知识的复杂性和经济活动的异质性等新的维度;二是在产业分工的基础上考虑到技术或知识分工等更加复杂的分工形式;三是关注被传统产业结构分析分解了的产业和产业要素之间的互动与融合特征。
现代产业体系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结构性分析概念,既要能够准确承接传统产业结构研究中的合理成分,也要充分认识到既有的产业结构研究与已经发生了深刻转变的经济现实之间日益严重的冲突,在推进理论创新的同时,为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更有力的分析工具。
01现代产业体系对产业结构概念的继承
在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转型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问题受到了研究人员和政府部门的极大关注,产业结构研究成果和产业结构政策层出不穷。然而,当产业结构概念被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大规模快速传播的同时,也逐渐出现了该概念被泛化、甚至滥用的倾向。这种泛化和滥用集中表现为一些研究成果和产业政策对经典产业结构研究基本假设和核心命题的偏离和曲解。因此,我们认为,在对传统产业结构研究进行批判和拓展之前,首先需要澄清国内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中有关经典产业结构问题研究的常见误读,还原经典产业结构研究的合理假设与命题。而有意义的产业体系研究的起点正是通过充分吸收和继承经典产业结构研究中的合理成分实现去伪存真。
继承一:结构性分析是一个长期性问题。
在经典的产业结构研究中,产业结构问题是长期发展问题,而不是短期增长问题。Syrquin在其《结构转换的模式》一文中开篇就强调,“经济发展的过程可以视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结构转换过程,……,(而)结构转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产业结构指的是从产出或要素使用的角度度量的部门在经济总体中的相对重要性,由于产业结构研究将“部门”作为分析的主要对象,因此,经济活动逐渐以“产业”的形式来组织的过程、即工业化(或产业化)过程成为产业结构变迁的核心或动因[1]。产业结构的变迁受到长期的需求结构变动、长期的收入水平变动以及制度结构变动等长期因素的影响,正因此,经典的产业结构研究总是利用长期的时间序列数据来测度需求、收入等长期自变量及其对长期产业结构变动特征的影响。例如Syrquin和Chenery在其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表的一系列成果中,基本上都使用了30年左右的多国时间序列数据。然而反观国内,相当数量的学术研究和几乎大多数的产业政策文件都在“短期”的意义上使用产业结构概念。有些学者建言以调整产业结构作为解决短期经济增长问题的手段,有的规划、甚至国家级的规划将产业结构统计指标确定为相关部门年度工作业绩考核指标。这种将经济学中长期意义上的产业结构问题短期化的研究和认识,是造成调结构在中国现实操作中充满机会主义的重要原因。因此,现代产业体系研究和产业结构研究必须首先在学理层面回到长期问题研究的轨道上来。
继承二:结构性分析是一个动态问题。
经典的产业结构研究并没有给出刻画产业结构变迁的永恒不变的普遍模式,而是将经济发展视为一个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认为经典产业结构研究所揭示的产业结构变动特征是经济发展的标准模式或普遍模式的观点,往往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国内的产业结构研究中。这类研究常常将中国的产业结构特征(如国民经济中的三次产业比重、工业经济中的重化工业比重等数据)与经典的产业结构研究的主要结论进行跨时期的比较,将中国当期的产业结构与所谓可比时期(通常按照可比的人均GDP水平确定)的一般模式的差距视为中国的产业结构“偏差”,并将经典研究所揭示的产业结构变动特征视为将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普遍模式观点在国内学术界的一个表现,是将经典研究的主要结论作为中国产业结构问题分析的基本假设。例如,干春晖等在研究产业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时就直接“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2]。这类研究严重忽视了影响一国产业结构因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基本的假设是,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是相对稳定的,各国的产业结构变动模式是唯一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特征的变动是线性的。
然而,如果仔细回顾经典产业结构研究的逐步深化过程就可以发现,以Chenery和Syrquin(CS)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于产业结构变动是否存在“普遍模式”是非常谨慎的。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他们在不断利用更长的时期、覆盖更广泛国家的数据来修正所谓的产业结构变动模式[3][4][5][6]。Syrquin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后续研究中,仍然通过不断引入国家间贸易等因素努力使基于多国数据刻画的产业结构“模式”更加稳健。在我们看来,经典产业结构研究对于推进学术界对产业结构理解的贡献,不在于提供了一个一层不变的“模式”,而在于提供了一个不断内生化更多样产业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起点和参照系。例如,基于Syrquin和Chenery提出的方法,Haraguchi和Rezonja(HR)利用1963年到2006年135个国家的数据对产业结构变动特征进行的研究就发现,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人均GDP达到以2005年美元计算的13500美元左右(而不是CS研究得出的39000美元左右)就开始出现下降,即制造业与收入水平的关系是凸的、而不像CS研究所揭示的是线性的[7]。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CS采用的数据恰恰是样本国家处于快速工业化时期的数据,而HR的数据则覆盖了主要工业化国家工业发展更加完整的周期,体现了更加复杂的国家间产业分工和产业技术。可见,影响一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是多样化的,产业结构特征的呈现是动态的,并不存在唯一的产业结构变动模式。简单地拿一国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特征与所谓的标准模式对比并以此确定一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具有严重的误导性。
继承三:结构性分析是一个内生性问题。
在经典的产业结构研究中,产业结构是一个内生的结果或过程,而不是外生的原因。总体上看,经典产业结构研究的工作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揭示多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长期特征,另一方面是发掘导致这些特征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中,Chenery首先将收入和国家规模纳入到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分析框架中,在60年代中期以后直至70年代的研究中,Chenery及其合作者强调一国对特定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80年代Ranis和Hayami等学者的研究进一步引入一国的产业发展基础作为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1],而90年代以后Syrquin的研究则强调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可以看出,在经典的产业结构研究中,“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都不是外生变量,而是共同由复杂的供给和需求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的(结果)”[8]。更进一步,即便在看待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时,经典产业结构也没有把产业结构简单视为经济增长的原因。相反,经典产业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假设是增长与结构变迁是相互作用的” [1]。与经典产业结构研究背离、从而把产业结构外生化相关的一个错误认识,是把产业结构概念工具化,即将产业结构本身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并相应地过度强调产业政策和政府在促进产业结构变迁中的作用。而这些恰恰是经典产业结构研究者极力反对的。Chenery在谈及结构主义的政策含义时就强调“更多的注意力应当放在如何改进新古典基本模型的现实性、而不是主张结构主义的过度简化了的结构程式(structuralist formulations),……,结构主义的政策建议常常过分强调发展中国家有限的行政性政策工具”[9]。在经典产业结构研究中,产业结构的国家间差异是由外生的需求、收入、自然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等因素决定的,而产业结构的非均衡则是由部门间的要素回报差异导致的,如果产业结构的非均衡长期存在,则一定是由于存在较高的要素流动壁垒或产业调整成本;也就是说,产业结构的长期、严重不均衡是由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交易成本和壁垒造成的。因此,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机制,是创造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的基本条件,并通过形成有效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降低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本。如果过度依赖产业结构政策,反而会使政策本身成为结构调整的障碍。
基于对经典产业结构研究的理解,我们认为,现代产业体系概念在中国的发展,应当首先厘清产业结构研究中大量似是而非的假设和命题,通过借鉴和吸收产业结构分析中的合理成分,为现代产业体系研究和产业结构研究的对话和衔接创造条件。具体来说,在经典产业结构研究的语境下,对现代产业体系问题的基本理解,首先应当是一个长期发展问题,因而不宜与短期经济问题混为一谈;其次是一个国家特定性的动态问题,应当避免任何教条的国家间比较和照搬;最后是一个内生性问题,有关现代产业体系的刻画和分析不应简单作为产业政策的目标。
02 现代产业体系对产业结构概念的拓展
虽然产业结构研究曾经对于深化中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对经济问题的理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由于产业结构概念理论外延的不恰当泛化,能够继续从这个概念挖掘出新意的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越来越少,能够真正用这个概念清晰地启发经济实践的产业政策越来越少。一种建设性的学术态度,是在重新审视产业结构理论的基本假设的基础上,通过修正这些基本假设,来弥补理论概念和不断发展的事实之间的鸿沟。现代产业体系在理论上的提出,不是用一个更时髦的词汇替代一个已经泛滥的陈词,而是在提炼新的典型事实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概念的理论内涵和外延的谨慎拓展。
1.拓展一:产业结构的多维性
“结构红利”的逐渐减弱,使传统产业结构研究的意义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产业结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问题一直是国内产业结构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该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总体上看,在这些研究中,分析的时期越接近转型后期,产业分析的层次越细分,研究发现的“结构红利”效应越不显著。例如,郭克莎、胡永泰、干春晖等等主要基于转轨早期的数据和/或三次产业数据的研究都发现,产业结构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10][11][12],郑玉歆对转轨初期(1980至1990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变动的研究也发现,制造业结构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13],然而针对转轨中后期的制造业产业结构(而不是三次产业结构)的多数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例如,吕铁利用1980至1997数据的研究显示,制造业行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不大[14],李小平和卢现祥利用1985至2003年数据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制造业结构变动并没有导致显著的“结构红利”现象[15]。
理论上讲,“结构红利”减弱可以有两种竞争性的解释,一种比较直观的解释是,随着我国产业结构日益完备,通过资源在产业间再配置提升总体生产效率的空间越来越小,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正快速由产业间配置效率向动态效率转变。这种解释可以说是目前国内产业结构研究的主流观点。但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传统产业结构研究的“结构划分”本身存在问题——传统产业结构研究的“结构划分”很可能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近年来中国经济真正的结构性特点。结构红利是否显著,不仅取决于配置效率和动态效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结构”或如何划分产业,不同的结构下,配置效率提升的空间很可能是不同的。除了前文提到的基于三次产业数据的研究和基于制造业数据的研究会发现不同的“结构效应”,来自哈佛大学的Hausmann和MIT的Hidalgo等教授的研究同样为我们提出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提供了重要启发。他们的研究显示,在过去60多年间,由工业产品复杂性所反映的一国制造业能力是所有预测性经济指标中能够最好地解释国家长期增长前景的指标,该指标甚至能够解释国家间收入差异的至少70%。[16]该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新理解产业结构的内涵,并采用了与传统发展经济学完全不同的产业属性测度方法。如果说Fisher和Clark的三次产业划分强调的是产品的物理形态,一般统计意义上的产业分类强调的是产品的技术相关性,Hoffmann对制造业的划分强调的是工业品的直接用途,Hausmann和Hidalgo等学者显然更强调从产业所依赖的知识的复杂性来识别产业的差别和定义产业结构;在测度层面,不同于传统的从产出或规模的角度来测度不同产业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他们从产业的知识复杂性或所体现的能力的角度来分析不同产业对经济发展的相对重要性。也正因此,他们得出了“虽然制造业的比重在发达国家并不高,但制造业、特别是那些复杂性制造业所体现的知识能力是决定一国长期发展水平”这一具有强烈结构政策含义的结论。
Hausmann等教授的研究事实上指出了现代产业体系研究对传统产业结构研究进行拓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即从针对现实问题的有意义的理论概念出发,而不是从照搬经典产业结构研究的既有结论出发,从新的结构视角来重新审视经济发展过程。除了Hausmann等人的研究外,以日本东京大学Fujimoto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创的基于产品架构概念的产业研究同样具有开拓性。他们创造性地将Ulrich教授提出的产品架构概念应用于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研究。通过利用产业一体化架构指数来测度不同产业的一体化程度(Integral Degree),他们发现了新的一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结构性特征——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的低一体化程度产业具有优势,日本在劳动密集的高一体化程度产业更具优势,美国则在知识密集的低一体化程度产业更具优势[17][18]。受该研究的启发,我们很容易提出一个新的有价值的中国产业结构问题,即未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任务,到底是在传统产业结构研究的语境下强调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和轻重工业结构,还是从能力和知识的视角出发加快发展那些更能够体现中国比较优势和动态优势的部门?Hausmann和Fujimoto等学者从产业发展的能力基础出发重新理解和测度产业的差异性,对产业结构变迁和国家间产业分工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彰显了创新性的产业结构视角对于经济问题分析的重要性,而这也正是现代产业体系研究进行拓展的重要方向。需要强调的是,近年来有关新的产业分类的研究,例如Margaret通过纳入共同需求和市场结构等因素的产业分类以及Hicks基于知识和生产一体化的产业分类,都非常重视微观经济行为特征对产业发展绩效和产业结构的影响。[19][20]总体上看,这些研究为探索新的产业结构分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为基于中国或跨国的产业结构经验研究提供了创新的机会。
2.拓展二:分工形式的多样性
传统产业结构研究遇到的第二个严峻挑战是不能很有说服力地回答中国经济学研究面临的一个日益突出的困惑,即为什么按照一般的产业结构评价标准,中国的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发达工业国家相比却始终存在巨大的差距。换句话说,中国向工业大国发展的过程,几乎完美地复制了经典产业结构研究所揭示的工业结构变迁的一般路径,但面对如何促进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问题时,经典产业结构理论和既有的产业结构研究都显得无力。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经典产业结构研究相对应的贸易理论主要是新古典贸易理论,而Heckscher和Olin利用要素禀赋和相对价格差异解释国家间分工的新古典贸易理论能够解释的仅仅是不同国家在产业层面的分工模式。按照经典产业结构和新古典贸易理论,高技术行业在国民经济和出口中比重的提升是产业升级的重要表现。事实上,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产业转移加速和加工贸易等新的分工形式的发展,以电子、信息、机械等为代表的传统上被认为是高技术或中技术的产业在我国工业和出口中的比重确实在快速提升。然而,经典产业结构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在一国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进入相对均衡状态时就几乎失去了解释力,因为要素结构的变动(如要素成本的快速上涨)与产业结构的相对稳定在新古典的理论世界中显然是不相容的。而事实上,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变动正逐渐进入这个阶段。“十一五”以来,我国工业出口结构呈现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主要行业的出口比重变动明显收窄、出口结构总体趋于稳定:以纺织服装、鞋帽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比重分别稳定在14%-16%和3%-4%左右的水平,以矿产品为代表的资源型行业的出口比重稳定在2%-3%左右的水平,以化工产品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出口比重稳定在4%-5%左右的水平,而以机电产品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比重稳定在55%-60%左右的水平。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国的工业出口结构由“极化”向“多元化”发展 [21]。
直观地看,新贸易理论似乎为特定阶段的产业结构稳定性现象提供了解释,即由于规模报酬、市场结构、需求差异等因素,国家间分工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转变。不同于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同一个行业在不同的国家是同质的,新贸易理论认为不同的产业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甚至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是异质的,在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的高技术行业主要是低端产品或低端细分产业。但新贸易理论的问题在于仍然不能刻画国家间的工序分工现象[22];而且,产业内贸易理论仍然不能为我们前文提到的产业结构稳定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卢锋提出的产品内分工理论所刻画的国家间分工模式更加符合现实的南北贸易特征,即由于外包和加工贸易等企业实践的发展,国家间的分工模式不仅向产业内、甚至向产品内转变。更重要的,产品内分工理论与产业结构稳定性现象至少是不冲突的,即虽然产业结构趋于均衡,但要素结构决定的产品内生产分工在发生变动。然而,产品内分工理论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分工格局和国际利益分配机制,即为什么不同的生产活动会分布在不同的国家,以及为什么有些生产性活动能够从全球分工体系中获得更高的价值?导致这种局限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品内分工理论仅仅考虑了生产性活动的国家间分工,对于更为深层次的、决定了生产活动分工的知识分工没有给予关注,而国家间能力的差异才是导致产业间、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差异的根源。
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很自然地找到另一个现代产业体系研究拓展的重要方向,即在更加微观的层面揭示隐藏在产业分工和产品分工背后的技术分工和知识分工模式。庆幸的是,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并不是空白,近年来有关产业架构(industry architecture)和技术集成(technology integration)的研究为这方面的拓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起点。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生产的分工不等于技术的分工。例如,在飞机发动机产业,虽然飞机发动机制造商将大量的零部件进行全球外包,但事实上总成企业在相当的核心零部件领域保留着技术优势,即飞机发动机制造商外包了零部件的生产,但并没有丧失有关零部件的技术能力[23];在电子信息产业,那些技术领先的生产企业虽然其生产线越来越窄,但其掌握优势技术的领域却越来越宽[24],同样,在化工产业和食品产业都存在类似的现象[25][26]。因此可以说,简单的产业分工和产品分工模式实际上掩盖了企业间和国家间远远更为复杂的技术和知识分工形式。虽然从产业或产品的角度看,发达国家企业将大量的零部件、甚至关键零部件生产外包给了中国企业,而且中国企业确实逐渐掌握了这些产品的生产工艺。但是从知识分工的角度看,概念设计和检测等关键能力仍然由领先企业掌握,仅仅是细节设计和工业设计等技术环节外包到了发展中国家。这种不体现为产品的技术集成能力是产业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都无法刻画的。
从更加微观、更加多样化的国家间分工形式来观察和分析产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从而国家间的分工和经济结构变迁问题至关重要。无论是李嘉图的贸易理论和新古典的贸易理论都将经济发展过程视为各种要素逐渐累积的过程,而产业结构变迁仅仅是要素累积的自然结果。正因此,按照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预见,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即便有可能向发达国家“收敛”,也绝不可能实现超越。显然,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工业发展史上屡屡出现的结构性产业赶超、甚至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赶超。解决这种理论困惑的一个重要思路是重新理解决定产业竞争力的各种要素的独特属性以及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制度不是相对于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另外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而是让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生产性要素发挥作用并决定了要素间战略互补性关系的组织载体;另一方面,不同于其他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制度能力的提升不是一个“连续变化的累积过程”,而是一个“非连续变化的创新过程”。由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忽略了要素之间的异质性,忽略了不同的组织能力能够让相同的要素产生完全不同的生产效率,因此虽然传统国家贸易理论对于理解后发国家的经济起飞问题提供了洞见,但对于回答经济起飞阶段之后的经济赶超问题却缺乏解释力和政策含义。因此,在作为微观行为的结果而表现出来的产业结构问题背后,实际上是现代产业体系研究对于产业竞争力来源问题的重新思考: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基于特定制度基础而被“组织”起来的要素累积过程,只有将要素的异质性、要素之间的匹配、制度结构和组织能力等更加丰富的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来,才能更准确地理解结构变迁和产业发展的真实过程[27]。
从现代产业体系对产业结构的拓展一和拓展二可以看出,现代产业体系并没有试图否定结构性分析的意义,而是强调从不同于传统的统计意义上的、更加多维度的产业结构视角来观察经济发展过程,可以从不同于传统的仅仅从产业层面、而是从更加微观的产品和知识分工的角度来观察经济发展过程。因此,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产业体系研究的目标是寻找不同于传统产业结构分析的、更能够解释经济发展本质和包容新的经济现象的“结构”分析框架和工具。如果放弃了“结构”分析,现代产业体系最终会像产业结构一样变成一个包罗万象、但实际上不知为何物的概念。
3.拓展三:产业边界的模糊性
传统产业结构研究的另一个基本假设是,产业边界是可以清晰界定的。该假设不仅体现在我们前文分析的有关产业结构变动模式的实证研究中,而且反映在有关主导产业选择这类规范性的产业结构研究中。主导产业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刻画主导产业的经济学和统计学性质,其中最有影响的定量标准当属筱原基准(收入弹性标准和生产率增长标准)与赫希曼基准(产业关联度标准)。尽管在现实的产业政策实践中,这两个基准并没有成为主导产业选择的教条,但不可否认,这两个基准确实是产业结构研究者和政府管理部门思考主导产业问题的主流逻辑。在产业结构不完备、很多重要的产业部门仍然处于快速成长期、行业间的生产率差异较为显著的时候,这些标准确实为产业结构研究和产业政策设计提供了简单而有效的工具。然而,随着我国的产业结构日益完备、各类型行业逐渐接近均衡增长状态时,这类研究的内在逻辑缺陷和负面影响逐渐显露。其中,筱原基准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考虑产业之间的相互影响。基于筱原基准的产业结构研究的一个简单表述是,应当优先发展那些生产率增长更快的产业。按照这种逻辑,一国的总体经济效率最优的状态,就是不断扩大高效率部门的比重,直到所有部门的边际效率相同。这种预设了产业之间是完全独立的、产业发展没有外溢效应的产业结构思维由于没有考虑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和外溢效应,因此其基于产业间比较效率研究得到的结论并不能为确定正确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提供有价值的指导。
赫希曼基准虽然注意到了产业之间的相互影响,但由于赫希曼基准仅反映了产业间用增加值测度的“投入产业”关系,因而这种供给需求意义上的关联性仅仅反映了产业间统计层面的、作为结果表现出来的产出依赖关系,而没有揭示产业之间投入产出背后更加复杂的知识依赖和能力互补等外溢效应。以新兴产业为例,新兴产业对于经济发展和国际间产业竞争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其本身创造或因形成新的需求而拉动创造的经济价值,更体现在新兴技术以及体现这些技术的装备在其它产业的广泛应用所引致的整个工业部门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例如新兴产业中的新材料、工业生物以及工业机器人等“通用技术”和设备,虽然其本身的市场规模不大,但由其广泛应用引发的新工艺、新装备及极端制造和精细制造能力却常常是决定整个产业链竞争力的瓶颈和节点。
产业互动的另外一种形式是产业内部各价值链环节之间的互动,例如研发与制造之间的相互作用。遗憾的是,目前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是西方学者对如何通过增强制造能力来进一步加强其创新能力的研究,而国内有关如何利用中国既有的制造优势提升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却几乎是空白。例如,Pisano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多晶硅在生产工艺方面与电子制造具有很高的相似性,而由于电子制造向亚洲的外迁,使得美国在多晶硅领域诸多的原创性技术也逐渐向亚洲转移,最后使得美国在该领域的技术优势和产业竞争力逐渐丧失。Pisano及其合作者基于翔实的案例研究还揭示了美国电子显示、锂电池、计算机和通讯等诸多产业的研发能力如何由于制造的外包和转移而受到损害[28]。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反映了两种形式的产业互动,一是由于具有相似的制造工艺,传统产业的发展能够影响到新兴产业的发展,二是由于制造和研发的融合,产业内部的制造和研发之间形成相互增强的互补效应。受他们的研究的启发,我们很容易提出诸如如何利用中国日益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加速吸引科技要素向中国的集聚、如何将传统产业积累的优势嫁接到新兴产业的发展等有意义的问题,而这些恰恰都是在现代产业体系标题下应当重点深化研究的问题。
由于技术进步和商业组织模式创新,导致传统产业边界越来越模糊化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产业融合。产业融合使得统计意义上并不属于同一行业的企业变成直接的竞争对手,产业组织结构呈现出鲜明的动态化和生态化等系统特征,传统的基于市场集中度和市场势力的市场结构分析失去了解释力。产业融合实现的一个重要方式是产业平台的形成。例如智能手机领域的苹果和谷歌、视屏游戏中的微软和索尼、电力系统领域的EV和Hydrogenics等,都是各自领域中的平台型企业,围绕这些企业和产品形成的产业都是平台化的生态系统组织方式。相对于市场边界清晰的传统产业,产业平台生态系统的特点,一是存在大量的围绕平台的互补品,而这些互补品(如零部件、数字内容、应用软件、广告等)往往来源于统计意义上完全不同的行业;二是存在显著的网络效应,即无论从技术还是价值创造还是利益分配的角度,这些互补品与平台之间、互补品之间、以及平台和互补品与消费者之间都由于显著的网络效应被紧密连接在一起;三是产业平台往往向用户提供同时包含了产品和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这种整体性的解决方案很难清晰地界定属于工业品还是服务品[29]。
因此,现代产业体系对产业结构概念的第三个拓展体现在,现代产业体系在承认结构分析的意义并不断努力发现经济系统新的结构特征的同时,也强调被特定结构所分割了的部门和产业之间的互动和融合。而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背景下,这种针对产业间、甚至产业内部不同价值环节之间的互动和融合的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03 结语
现代产业体系问题在理论上的提出和发展,既是产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配置效率向动态效率转变、中国的产业发展模式由多国普遍模式向中国独特模式转变的客观要求,是中国进入产业结构体系已经比较完备、产业增长开始趋于均衡、产业发展需要探索新的动力和方向的特殊阶段时的客观要求。
我们主张在继承和吸收、而不是舍弃经典产业结构研究的基础上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概念,我们主张通过清晰刻画概念的理论内涵、而不是以包容所有理想成分的方式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概念。一方面,尊重经典产业结构研究的传统,现代产业体系问题应当在长期、内生和动态的层面进行研究;另一方面,现代产业体系研究应当能够很好地解决传统产业结构研究的基本假设和主要命题与变化了的典型事实之间日益严重的的冲突。基于此,相对于传统的产业结构概念,现代产业体系概念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独特性:一是三次产业结构、轻重工业结构等传统的产业结构划分方法并不是对经济系统进行结构化分析的仅有的视角,产业所基于的知识的复杂性和经济活动的差异性同样能够为产业结构理论和经验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洞见;二是 “产业”层面的分工仅仅是国家间分工的一种形式,国家间的分工形式是多层次的,传统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研究常常掩盖了国家间更为复杂的产品内分工及越来越重要的技术分工问题;三是产业之间的边界并不总是可以清晰界定的,在对经济系统进行有意义的结构化分析的同时,必须同时注意被分解了的产业要素之间的互动和融合特征。现代产业体系问题研究的要旨在于,从理论能够更好地反映变化了的典型事实这一基本原则出发,通过对经济现象进行创新性的结构分析以及对被各类结构分析分解了的产业、产品和经济活动之间的互动融合关系的分析,最终实现对经济现象的系统性认识。
需要强调的是,与传统的产业结构概念不同,现代产业体系概念的外延并不是可以简单用少数统计指标来测度和刻画的,从而大大增加了现代产业体系在经验研究和实践操作中的难度。然而,这也许正是当前发展阶段中国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必须直面的问题。当中国经济已经跨越了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经济发展越来越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时,有意义的经济发展战略应当更多地从自身的特定性和国家间发展模式的差异性出发来思考产业发展问题,即在新的发展模式下,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部门都必须适应更加复杂的分析框架和决策模式。
参考文献:
[1]Syrquin, M., "Patterns of structural change," in Chenery H., & T.N. Srinivasan (ed.),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ume 1,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1988, 203-273.
[2]干春晖等,《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载《经济研究》,2011(5),4-16。
[3]Chenery, H., “Patterns of Industrial Gro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0, 50(4), 624-654.
[4]Chenery, H., and L. Taylor, “Development Patterns: Among Countries and Over Tim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68, 50(4): 391-416.
[5]Chenery, H., and M. Syrquin,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1950–197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6]Chenery, H., and M. Syrquin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1950 to 1983,”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WDP41, 1989.
[7]Haraguchi, N., and R., Gorazd,"In Search of General Patterns of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UNIDO working paper, 2010.
[8]Matthews, R.C.O., "The Economics of Institutions and the Sources of Growth", Economic Journal, 1986, 96(2), 903-918.
[9]Chenery, H., "The Structuralist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5, 65(2), 310-316.
[10]郭克莎,《三次产业增长因素及其变动特点分析》,载《经济研究》,1993(2),51-61。
[11]胡永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的首要作用》,载《经济研究》,1998(3),33-41。
[12]干春晖等,《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演进与生产率增长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09(2),55-65。
[13]郑玉歆,《80年代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变动及其来源研究》,郑玉歆等《体制转换中的中国工业生产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4]吕铁,《制造业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载《管理世界》,2002(2),87-94。
[15]李小平、卢现祥,《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变动和生产率增长》,载《世界经济》,2007(5),52-64。
[16]Hausmann, R. & C.A., Hidalgo, et al. . “The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Mapping Paths to Prosperity,“ CID Harva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2011.
[17]Fujimoto, T., & O., Takashi,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Hypothesis of Architecture bas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MMRC working paper, 2006.
[18]Fujimoto,T., & S., Yoshinori, "Inter and Intra Company Competi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 Competition: A Micro and Macro Interpretation of Ricardian Trade Theory.” 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11, 8(1), 521-534.
[19]Margaret, D., "A Systems-based Approach to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Policy, 2007, 39(10), 801-813.
[20]Hicks, D., "Structur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s Dynamics, , 2011, 22(5), 265-278.
[21]宋泓,《未来10年中国贸易的发展空间》,载《国际经济评论》,2010(1),55-64。
[22]卢锋,《产品内分工》,载《经济学季刊》,2004(4),56-72。
[23]Prencipe, A.,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Product Evolutionary Dynamics: A Case Study from The Aero Engine Industry," Research Policy, 1997, 10(25), 834-845.
[24]Gambardella, A., and T., Salvatore, "Does 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 Imply Convergence In Markets? Evidence From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Research Policy, 1998, 5(27), 456-467.
[25]Brusoni, S., and A., Prencipe, "Unpacking the Black Box of Modularity: Technologies, Products, Organisation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1, 2(10), 234-246.
[26]Von Tunzelmann, G. N., "Localised Technological Search and Multi-Technology Companies,"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1998, 3(6), 201-215.
[27]贺俊、吕铁,《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政策概念到理论问题》,载《财贸经济》,2012(5),106-113。
[28]Pisano, G., & W., Shih, Producing Prosperity: Why America Needs a Manufacturing Renaissance,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12.
[29]Cusumano, M., Staying power, Cambri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